- 對,就是這幸福的感覺 ——《皖韻八記》中的行走和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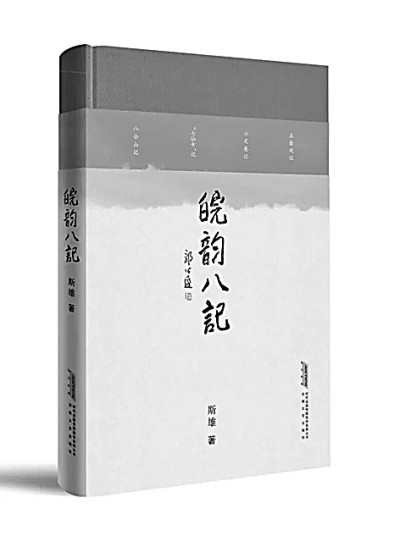
《皖韻八記》
斯 雄 著
安徽文藝出版社
【光明書話】
不管是否承認,一生當中,每一個人都在行走,在行走中迷失方向,在行走中目光堅定。哪怕是駐足發呆,那也是另一種行走,思緒的行走,甚至,有的時候,思緒的行走遠比腳步的行走更有意義。
無一例外,中國的文化散文都是行走的發現,再推而廣之,世界上一切文史哲的成果都是行走的結果。“每每尋訪遺跡、翻看方志史料的時候,總不免讓我感嘆古人的了不起。”斯雄在他的新作《皖韻八記》“自序”中這樣説的時候,他的行走已經具有了澄澈的意味。中國的傳統文化外化于山川古建,內凝于典籍經史,甚至,像或明或暗的微星一樣藏在粗樸的族譜和簡陋的鄉間文書裏。這就使得中國的文化愈發博大精深,而且玄機暗藏。“隨物賦形,人與山尚且能對上眼,説明確實有物我兩忘、身心俱悅的歡喜。”我就説嘛,《皖韻八記》與其説是斯雄先生《徽州八記》和《江淮八記》的續篇,不如説是他在行走中更多的發現,是更通透的“歡喜”。
中國文化講求天工開物、道法自然。如果把各類生物也視作自然的一部分或自然的衍生物,其實人類是應該和各類生物成為朋友並從萬物中汲取智慧。在我的故鄉亳州市中心,矗立著一尊華佗的雕像,行色匆匆的華佗腰間挂著丹藥葫蘆,目視前方,一臉憂色。在亳州,最為當地人頻頻提起並報以最大敬意的就是鄉賢曹操和華佗。而亳州之所以成為“中華藥都”,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華佗。每次仰視那尊雕像,我都在想,華佗留給亳州的,難道就是這樣一份名號?
這個問題一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才有了明晰的答案。一個流傳頗廣的視頻顯示,在武漢市一個方艙醫院裏,來自亳州市中醫院的一名醫生帶領患者和醫務人員練習五禽戲。很慚愧,自己在亳州的土地上行走了幾十年,竟然對五禽戲熟視無睹,竟然對華佗留給後人的這份豐功偉績視為當然。
而同樣行走的斯雄卻以如炬目光發現了這則信息背後的宏大敘事,他在《五禽戲記》一文中,由這則信息生發,對五禽戲的歷史進行了爬梳,讓習練五禽戲的功效與一度困擾人類的新冠病毒碰撞,“在疾病面前,人類其實是很脆弱的。真要直面生死的時候,人的想法反而變得簡單了。首要的當然是活下去,進而肯定也會想到;早該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啊!”
這是振聾發聵的喟嘆。在面對災難的時候,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路徑會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但我們在期待春暖花開的時候,是否道法自然?如果不能做到,是否退而求其次,去師法前人的優秀遺産?所以,行走的另一面,就是把個體打開,去除人為設定的枷鎖。當然,這同樣需要腳力、眼力、腦力、筆力。因為生活從來不在別處,生活就在眼前,觸手可及卻又需時時追尋。
還是2020年,淮河遭遇歷史上最大洪水。7月20日8時32分,“千里淮河第一閘”王家壩閘自1953年建成後第16次開閘,咆哮洶湧的洪水被“牽”進本為良田的蒙洼等7個蓄洪區。“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蘇,這一次,又是蒙洼人含著眼淚扛起所有”,各種媒體上,類似的悲壯故事被反復提及。
開閘的那一歷史時刻,我是在現場的,出於職業需要,也在第一時間采寫了報道。當時,斯雄先生也因為工作緣故在現場。但之後不久,他又寫了《王家壩記》,把看似新聞的邊角料整合出一篇極具史料價值和當下意義的作品,既有作者身臨其境的獨特感受,又有淮河和王家壩歷史的變遷,最難得的是那種伴隨著情緒的跌宕起伏後的理性思考。
“遙看王家壩閘,如巨龍橫臥在蓄洪庫上游,確有拒水于千里之勢。站在閘的橋面上,雖然腳下洪水仍在咆哮,但已然不再感覺那麼驚心動魄、提心吊膽了。”沒有到過王家壩,沒有親歷開閘那一刻的緊張焦慮,絕不可能有如此真切的感受。更不為人所知的,是流淌著災難和苦難的淮河從“十年九澇”到如今的安瀾,背後是久久為功的治理和智慧,“人和水都有了出路,不再爭奪發展空間,自然就能和諧相處了。”
新聞是對現實的燭照和呈現,文化散文如何介入現實併為現實“兼收並蓄”,可能是當下很多書寫者必須要思考的問題。你可以因草木而歡喜,可以品茗而自得,可以經山川而自樂,問題在於,如何把小歡喜變成大歡喜,如何把一人之樂演繹成眾人之樂,如何把個體自得上升為全體自得,一方面需要腳步向前,另一方面,恐怕還要把視線從內向轉為外向。具體地説,新聞界慣常使用的“宏大敘事和微小切口”的合一,可能是對現實最好的表達。
我一直認為,斯雄先生的職業習慣成就了他的行走,練就了他的深邃,而對文字的敬惜和執著,又讓他的行走和行走中的發現有了厚重且色澤濃郁的“包漿”。《皖韻八記》中的《天柱山記》《六尺巷記》《“七仙女”記》《八公山記》等,莫不如此
得知他要寫《天柱山記》,我是很為他捏了一把汗的,誠如作者所言,“一山而多名,背後一定有文章”,同理,一山而多名,先後一定也有無數名人“留下文章”,比如余秋雨的《寂寞天柱山》對很多試圖品讀天柱山的人來説就是一座“大山”。但斯雄先生另辟蹊徑,把眼光投注到天柱山下三祖寺旁的摩崖石刻上,尤其對“止泓”兩個大字情有獨鍾,這就很符合登山觀景的意趣了——埋頭登山,移步換景,唯於心儀的景色前久久流連,心心唸唸。一番和“止泓”遍歷千年的對話和會心之後,“心中默念‘止泓’,回看天柱峰,不免有望峰息心之慨。盤桓山谷泉邊,仿佛照見了自己的影子,不知不覺中,真要‘坐石上以忘歸’了”。
這一番,登山如行雲,文字如流水了。
休謨在《人性論》中説:“當你能夠感覺你願意感覺的東西,能夠説出你所感覺到的東西的時候,這是非常幸福的時候。”我同意。也因此堅定地認為斯雄是幸福的。
據説,坐了江山後,朱元璋對劉伯溫説,原本是打家劫舍,不承想弄假成真。第一本《徽州八記》後,斯雄曾言之鑿鑿地謙稱“遊戲之作”,誰知不久又有了第二本《江淮八記》,接著在他離開安徽後又推出第三本《皖韻八記》,而且篇篇是精品,篇篇被廣為傳誦。這種“弄假成真”,幸福的意味可想而知。
疫情期間,已經“行走”到吉林的斯雄通過微信發來一張照片,一改昔日的清癯,有些微胖了,襯以雜沓的鬍子,反倒有那麼一絲仙風道骨的意蘊了。他自嘲是“封城居家辦公的老人”,呵呵,這個人,分明是居家卻放飛思辨行走不已的小老頭嘛。(作者:常河,光明日報高級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