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撞沉《太平輪》
| 編輯: 陳豪 | 時間: 2014-12-15 10:49:31 | 來源: 東方早報 |
我們還可以質疑,為什麼《泰坦尼克號》可以把人物群像的來龍去脈與船上的故事主線細密交織,要階級有階級要愛情有愛情,而《太平輪》就非要拍成上下集。發展了這麼多年的影像敘事,順敘倒敘插敘閃回都放在那裏,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你何苦還要上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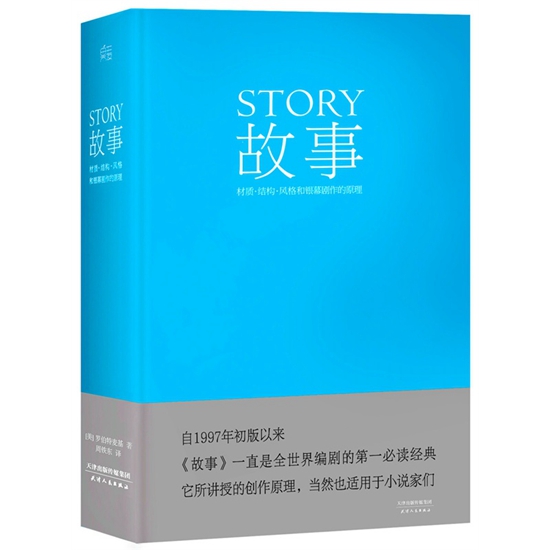
《故事》[美]羅伯特·麥基著周鐵東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544頁,68.00元

《太平輪》在起錨之前,差不多已經被《故事》裏的所有創作定律結結實實地撞沉。
《西雅圖未眠夜》是不是一部愛情故事片?這個看起來不可能有異議的問題在羅伯特·麥基的《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劇作的原理》中卻得出了別樣的結論。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發生在影片末尾而不是開頭,所以“這並不是愛情故事,而是渴望故事,因為關於愛的談論以及愛的慾望充斥了所有場景,將真正的戀愛行為及其不無磨難的後果留到銀幕之外的未來發生。也許事實是,二十世紀親手創造卻又埋葬了這個浪漫時代”。
這一段出現在《故事》第三章“結構與背景”中,用來説明如何“向陳詞濫調宣戰”,如何在精通類型的基礎上“再造類型”。可以給麥基補充的一點是,《西雅圖》中反復提及並致敬的另一部電影《金玉盟》,正是被《西雅圖》的編導諾拉·艾弗朗“精通”並“再造”的類型經典。《故事》寫于1997年,如果麥基今年碰巧看到了寧浩的《心花路放》,或許會樂於在他來中國開高價培訓班的時候再“現挂”一兩句。《心花》從一開始就按男女主角兩條線分開敘事,讓熟記《西雅圖》的文藝青年胸有成竹地認定:黃渤和袁泉一定會在影片的某個時間點邂逅于大理,很可能是在結尾。我們沒有猜錯,他們確實在結尾才相逢,但寧浩利用蒙太奇時態陷阱玩了一把《西雅圖》的逆向結構:他們的邂逅其實發生在幾年前,你以為同時進行的兩條線其實處在不同的時空中。袁泉站在過去,漸漸向那場“邂逅”靠近;黃渤立於當下,打著公路獵艷的幌子收拾當年“邂逅”造成的心理殘局。至於麥基所説的“真正的戀愛行為及其不無磨難的後果”,同樣被留到了銀幕外,發生在這兩段時空之間。隨著結尾黃渤在舊愛的婚禮上以相同的程式邂逅新歡,舊故事的幻滅便與新故事的開端完成了重疊,而前者又對後者的未來構成反諷。如是,這一路其實走完了一個封閉的圓環,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麥基在《故事》一書中所讚賞的“故事達到負面之負面”。
在故事的王國中,愛情類型顯然是被徵用最多、資源近乎枯竭的領地之一,因而説書人在這塊領地上的每一次破繭重生都格外艱難。我們重走從《金玉盟》到《西雅圖》到《心花》的那條暗道,約略可以窺見編導在拿捏分寸時的如履薄冰,在觀眾對故事的原始模型(archetype)的心理依賴和喜新厭舊之間尋找愈來愈窄的交集——這差不多也是《故事》一書在各個章節中用不同節奏反復吟唱的主旋律。
與其他論述戲劇文學或者創意寫作的書籍相比,《故事》幾無學術創見,也不像很多大作家的文學演講那樣充滿不可思議的比喻和如同天啟神諭般的使命感(想想《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吧)。甚至,在有些段落,它淺近得有點拿不住范兒,激情上頭時會來十幾個排比句(“對故事的愛……對真理的愛……對知覺的愛……對夢想的愛……”),多少透出一點“成功學”文體的影子——當然,你也可以把這看成是一種戲倣。麥基從不諱言他本人的編劇經驗並不豐富而且水準只能算二流(但他認為,這並不妨礙其成為“最好的編劇教練”);同樣地,在這本書裏,他在表述觀點時也基本上不會含糊其辭。比方説,儘管在劃分類別時也算面面俱到,儘管説過不少英格瑪·伯格曼的好話,但麥基對電影行業的“高大上”區域總體上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對歐洲片、新浪潮、反情節、作家電影之類的概念也不無揶揄。隨手翻翻,就會有這樣的冷槍冒出來:“反情節的製造者對欲語還休的描寫方式或暗度陳倉式的收斂幾乎沒有興趣,相反,為了昭示他的革命雄心,他的影片傾向於過度鋪陳和自我意識的大肆渲染。”
也許,正是這種旗幟鮮明的態度,賦予了這本書最顯著的特點:在他近乎布道般的鼓吹中,在他熟諳現代商業法則的推銷中,企圖重建的是人們對故事的信仰——無論這種信仰裏含有多少功利的成分。麥基知道,你跟現代人追溯荷馬、拉伯雷,緬懷大樹底下的説書人,他們會一臉漠然;但是如果你煞有介事地拿出一組圖表,賣力地為他們計算盈虧比,指導如何解放故事的生産力,催眠效果就會立竿見影。所以我們常常能在《故事》中看到仿佛能精確量化的句子:
“隨著故事設計從大情節開始向下滑行到三角底邊的小情節、反情節和非情節時,觀眾的數目將會不斷縮減。”“一個故事,即便在表達混亂的時候,也必須是統一的。” “根據行家的經驗,主情節的第一個重大事件必須在講述過程的前四分之一時段內發生。”“一個重復的情感只能産生預期效果的一半,如果再重復一次,其情感負荷就會不幸發生逆轉。”“主人公必須具有移情作用,同情作用則可有可無。”“一個故事中兩個最強烈的場景往往是最後兩幕的高潮,在銀幕上,它們常常僅隔十到十五分鐘,因此不能重復同樣的負荷。如果主人公得到了他的慾望對象,使最後一幕的故事高潮成為正面,那麼倒數第二幕高潮則必須是負面。你不能用上揚結局來鋪設上揚結局,也不能用低落結局來鋪設低落結局。”“改編的第一條原則是:小説越純,戲劇越純,電影就越差。”
這些“必須”或“不能”是否能涵蓋所有的故事形態,究竟有多少可操作性,其實很難一概而論。同樣地,《英國病人》和《三十七度二》(書中譯作《巴黎野玫瑰》)的擁躉(我就是)也一定會因為麥基對這兩部電影的偏頗之詞而略生反感。我們甚至完全可以拋出那個萬能的句子——“故事永遠存在另一種講法”,來抗議麥基妄圖壟斷“故事話語權”的野心。不過,好玩的是,在整個閱讀過程中,每當我準備質疑麥基的投機取巧時,總會被某些擾人的觀影經歷逼回他的文本前,並在心裏暗暗承認:如果能做到三成,那麼,我國影視行業的優等生未必會增加,但及格率還是有可能顯著提升的。換句話説,跟著麥基未必真能學會怎樣講出一個好故事,但起碼會比以前更容易辨別一個壞故事。
比方説,差不多已經成為今年國産劇新標杆的《北平無戰事》,為什麼仍然在很多方面讓人骨鯁在喉?大量細節不靠譜、節奏拖遝、場景轉換遲滯生硬,這些問題到底能否與其借古諷今、激動人心的“大概念”(big idea),抑或代表國家級水準的表演割裂開來看?當我們隨口説上一句“瑕不掩瑜”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些“瑕”的産生,很可能就是因為“瑜”先天不足,有許多失真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細節塞進了或許並不成立(至少,其是否成立尚有待論證)的故事框架。如果劇本提供的東西不夠紮實,那麼演員就只能調動更多的“演技”去憑空發揮,有時漫無邊際,有時歪打正著,但都會像顯微鏡一樣放大故事本身的空洞——甚至可以説,演員越好,演技越精湛,這種放大效果就越明顯。一個故事,如果光有“道路自信”而沒有“細節自信”,那麼就只能採用單一的手法反復灌輸宏偉的主題。因此,並不是建豐同志除了打電話不會幹別的,而是講故事的人只顧著被自己的理念所感動,卻忘了手裏缺乏足夠的材料來貫徹這種理念,支撐不出更形象更有説服力的細節來推動情節發展。按照麥基的説法,一切陳詞濫調都可以追溯到同一個原因,而且也是唯一的原因:作者不了解他故事中的世界。造成“索然無味的講述”的原因,往往是知識的膚淺。
在這方面,《太平輪》的問題比《北平無戰事》要嚴重好幾個數量級。在片中的船起錨之前,差不多已經被《故事》裏的所有創作定律結結實實地撞沉。當片中所有人物都在八十年代的節奏中“起范、音樂、定格”時,我們只能報以嘆氣、哄笑或者睡覺。我們當然可以嘲笑宋慧喬只會光著腳轉圈,譴責黃曉明只會歪著嘴微笑,説他們只偶像不實力繡花枕頭一包草,但我們更得問一問,編劇究竟給人物提供了什麼樣的支持。在麥基看來,人物的塑造與故事的結構根本就是一回事,漂亮緊湊的故事線自然會把處於壓力之下的人物的本性一步步揭示出來,反之亦然。同樣的,對白的好壞與故事的優劣也密不可分,“一個手法精巧而對白粗劣或者描寫枯燥的故事是非常罕見的,更多的情形是,故事手法越是精巧,其形象則越生動,對白也越尖銳。故事進展過程的缺乏、動機的虛假、人物的累贅、潛文本的空洞,情節的漏洞以及其他類似的故事問題,才是文筆平淡乏味的根本原因。”所以説,當我們從長澤雅美的信、黃曉明和宋慧喬的日記以及片中絕大部分人物的對話裏聽不到哪怕一個新鮮的、冒著活氣的句子時,我們首先應該懷疑的,不是“編劇的作文是體育老師教的”,而是“他(她)根本沒做好編這樣一個故事的準備,他(她)不知道筆下的人物應該説什麼”。
一覺醒來,走出影院,當我們摘下那副本來就多餘的3D眼鏡時,我們的耳邊可以配上來自《故事》的畫外音:“故事講述已經淪為徒有其表、令人炫目的聲光奇觀,以免觀眾注意到故事本身的虛空與偽劣……銀幕充斥著華彩的攝影和用金錢堆砌的製作場景,然後用一個單調低沉的畫外音將形象串聯在一起,將電影這門藝術蛻變為過去曾經風靡一時的經典連環畫。”如果用這段話來形容《太平輪》,惟一需要修改的地方,是把“聲光奇觀”改成“婚紗攝影式的廉價審美”。進而,我們還可以質疑,為什麼《泰坦尼克號》可以把人物群像的來龍去脈與船上的故事主線細密交織,要階級有階級要愛情有愛情,而《太平輪》就非要拍成上下集。發展了這麼多年的影像敘事,順敘倒敘插敘閃回都放在那裏,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你何苦還要上下集?除了想多賺點票房,還有什麼別的原因?於是麥基的告誡再度響起:“我們習慣性地推遲主情節,在開篇序列中一味地充塞一些解説性的東西。我們一貫地低估觀眾的知識和生活經歷,用煩瑣的細節來展示我們的人物及其世界,而對於這些東西,觀眾往往僅憑常識便能知曉。”
“觀眾往往僅憑常識便能知曉。”這樣的説法是典型的麥基風格。事實上,“説書人”如何評估他們與觀眾的關係,也是《故事》中一個重要而有趣的命題。麥基始終把兩者置於一場動態平衡的拉鋸戰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當然,鋻於麥基是重建故事信仰的布道者,在他的暗示中,這場拉鋸戰的最終勝利者當然必須是説書人。為此,他不惜用了兩個略顯輕浮的比喻:其一,中世紀的農民偷獵鹿和松雞後,帶著戰利品穿過森林逃跑時,他們會用一條魚,一條熏鯡魚,在逃路上橫拖一下,以迷惑莊園主的獵犬。可想而知,這裡的“獵犬”指的是觀眾,而好故事的作者,一定要準備好那條香噴噴的熏鯡魚。其二,房中術大師們都知道把握做愛的進度,在“只差一點兒”的時候講個笑話,換個位置,吃個三明治,“以週期性升降的緊張度”達到欲仙欲死的境界。
“寬厚仁慈的講故事的人就是在和我們做愛啊,”麥基寫到這裡,已經忘乎所以,“他知道我們有能力達到那樣的高潮……如果他能掌握好適當進度的話。”
相關新聞
新聞推薦
- 多組數據看2025年中國外貿“含新量”“含綠量”“含智量”2026-01-16
- 生鮮果蔬、年宵花卉、特色美食齊上陣 節前消費新圖景活力涌動2026-01-16
- 2026年“鄉親相愛一家人”臺胞迎新春聯誼活動(寧德站)舉辦2026-01-16
- 台灣網友失散的親人找到了!90歲湖北老人隔海呼喚:“期盼侄孫回家”2026-01-16
- 四大洲花滑錦標賽下周北京上演 雙奧場館再迎世界級角逐2026-01-16
- 《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同款美食,這份早餐“攻略”裏都有!2026-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