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我的稿子有些煙火氣
| 編輯: 陳豪 | 時間: 2014-06-17 15:34:07 | 來源: 光明日報 |

艾青(資料圖)
第一次見到艾青是在1978年夏天。那年大陸剛開放,國僑辦主任廖承志邀請香港出版界代表團訪問內地(團長是香港出版家藍真先生),我也是代表團的成員。
第一站是首都北京,其中由官方安排的活動之一,是讓“文革”後新復出的文藝家與我們會面,畫家有李可染、黃永玉、華君武等等;作家、詩人有姚雪垠、賀敬之、臧克家等等。我與同行的香港詩人何達,滿以為在這個場合可以見到心儀的詩人艾青,結果艾青卻沒有出現。
持聶華苓所給的地址,我與何達在北京民族飯店雇了一輛車子,決定私訪艾青。車子穿街走巷地兜了好一會,終於在一條狹窄的衚同裏找到門牌。
原來艾青雖然返了北京,卻還未正式平反,到了翌年他才正式恢復榮譽和享有政治地位。我第一回見到心儀的詩人,也許因為太興奮了,真不知從何説起。艾青、高瑛夫婦因“撥亂反正”,恢復自由身,雖回到北京,臉膛仍流溢著新疆的陽光,紅彤彤的,加上他們熱情可掬,令人有一見如故之感。
高瑛滿臉歉意地説:“你們是遠客,沒有好東西招待。”説罷從雙架床床底摸出一個大西瓜送給我們,説是剛從新疆捎來,讓我們帶回酒店吃。
其景象今天憶起,仍歷歷在目。記得那次見面,艾青問我最喜歡他哪一首詩,我説了兩首詩名,一是《我愛這土地》,一是《時代》,後來艾青特別謄抄了《我愛這土地》給我做紀念。這首寫于1938年的詩,是艾青的成名作,表達了他對歷經磨難的祖國的深沉感情。
打從1978年認識艾青伉儷開始,我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繫,從未間斷過通函。雙方來往的信函,始初是由艾青親自執筆,後來均由高瑛代筆。
我在這裡選兩封艾青的親筆信。一封寫于1978年12月27日,一封寫于1979年4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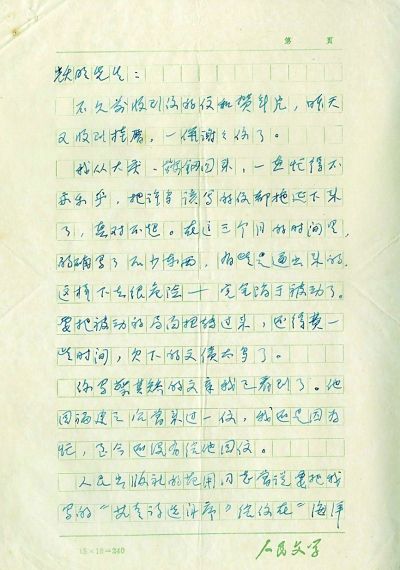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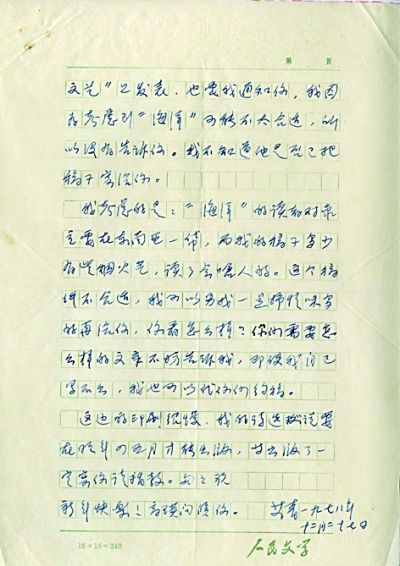
耀明先生:
不久前收到你的信和賀年片,昨天又收到掛曆,一併謝謝你了。
我從大慶、鞍鋼回來,一直忙得不亦樂乎,把許多該寫的信都拖延下來了,真對不起。在這三個月的時間裏,的確寫了不少東西,有些是逼出來的,這樣下去很危險──完全陷於被動了。要把被動的局面扭轉過來,還得費一些時間,欠下的文債太多了。
你寫蔡其矯的文章我已看到了。他回福建之後曾來過一信,我還是因為忙,至今還沒有給他回信。
人民出版社的范用同志曾説要把我寫的《艾青詩選·自序》給你在《海洋文藝》上發表,也要我通知你,我因為考慮到《海洋》可能不太合適,所以沒有告訴你。我不知道他是否已把稿子寄給你。
我考慮的是:《海洋》的讀者對象主要在東南亞一帶,而我的稿子多少有些煙火氣,讀了會嗆人的。這個稿件不合適,我可以另找一點抒情味些的再給你,你看怎麼樣?你們需要怎麼樣的文章不妨告訴我,即使我自己寫不出,我也可以代你們約稿。
這邊的印刷很慢,我的詩選據説要在明年四五月才能出版,等出版了一定寄你請指教。
匆匆祝新年快樂!高瑛問候你。
艾青1978年12月27日①
耀明先生:
來信收到,林信先生與“大一”設計公司經理由張仃陪同於臨走前一天到我家,吃了一頓極隨便的便飯,兩人拍了一些我收藏的冊頁,林信並送我一架錄音機與小型電子計算器,我都只好收下;他也帶來你給我的一罐高級咖啡,謝謝。
關於林信所贈的東西,請你給我出主意究竟如何報答才好,請你直説,因你是我的朋友,用不到客氣。
我的三國之行,是否路經香港不得而知,我個人當然很想能走香港,因我所到過的香港將過去了半個世紀,變化一定很大。如路過香港將拜訪你,也可以見見你的夫人。
《在汽笛長鳴聲中》剪報均已收到,勿念,錯字不少,只得由他去了。所謂稿費,請存你處。我和高瑛都準備給《海洋文藝》寫稿。
此間外文局出版的《中國文學》下期著重介紹我的作品,你如需要,等出版後將寄你。
去年一別又已半年,不知你何時能再來?
請告訴我:你需要什麼人的畫,只要是我熟識的人,我都可以代求。
順祝編安。高瑛問候你。
艾青 1979年4月24日②
這些信件,令我重溫起艾老待人的熱情、誠懇、寬厚與週到,我無比懷念!
作者注:
①艾青從新疆勞改返北京後,獲中國作家協會邀請參觀大慶油田和鞍山鋼鐵公司。我于1978年夏天在艾青家認識閩籍知名詩人蔡其矯,返港後,我寫了一篇《速寫抒情詩人蔡其矯》,發表在香港《新晚報·風華版》。發表後,曾寄奉艾老指疵。《艾青詩選·自序》即是《在汽笛長鳴聲中》。香港《海洋文藝》乃刊物,我曾在那裏當編輯,主編是吳其敏先生。
②《在汽笛長鳴聲中》是艾青復出後第一本詩集的序言,是高瑛大姐之前寄給我並轉送《新晚報·風華版》刊登,結果報紙出來後,發現有不少錯字。信中提到的《中國文學》是英文版,由作家鳳子的美國籍丈夫當主編。艾青早年在法國習畫,認識不少畫家。他問筆者需要什麼畫,我不便造次,所以一直沒敢請他代向畫家索畫。他後來在1979年赴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途次香港,捎了一幀張仃的焦墨山水畫給我。
相關新聞
新聞推薦
- 習近平春節前夕慰問部隊 向全體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武警部隊官兵軍隊文職人員預備役人員和民兵致以新春祝福2026-02-13
- 王毅:做到“五個共同”,深化中匈友誼,拓展互利合作2026-02-13
- 外交部:“倚外謀獨”是蚍蜉撼樹 註定失敗2026-02-13
- 全球看春晚!總臺“春晚序曲”俄羅斯專場活動在莫斯科舉行2026-02-13
- 國際銳評丨從“圍觀”到“融入”,感知馬年春節裏的中國文化密碼2026-02-13
- “兩岸一家親 真情助企行”——2026年迎新春臺企特色産品展銷會開展2026-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