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爭遺孤王林起:日本和中國是我的兩個祖國
| 編輯: 關春英 | 時間: 2015-09-08 17:04:05 | 來源: 北京日報 |
陳援
上世紀70年代,日本戰爭遺孤王林起沒有申請回國。原因是他説不清自己在日本的情況了。
直到8年以後,他想起了中國養父的遺願,抱著試一試的想法,才去和日本駐華使領館聯繫確認身份。
經歷兩年的時間,日本使領館居然找到了他在日本的戶籍檔案。臨行前,養母握著他的手説:“你對我們家的義務已盡完了,放心走吧,不用回來了。”林起明確地告訴養母:“我一定會回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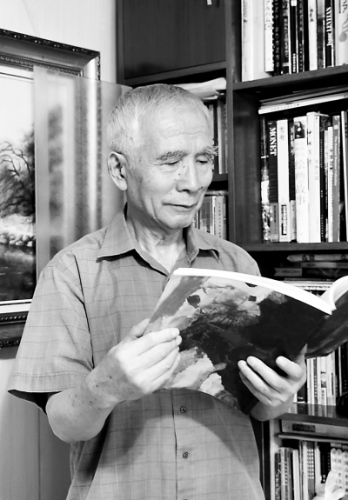
1 故鄉、童年和母親
1935年8月20日清晨,一個男孩子出生在日本山形縣東置賜郡高畠盯和田村一個普通農戶的家裏。
這孩子是渡部家獨子延雄的長子,取名宏一。在宏一幼時的記憶中,父親時常不在家,是母親白石貞帶著他在外祖父母家長大。
外祖父家的老祖宅高大寬敞,大廳堂的中間有個炭火池。白天用它燒水煮飯。冬天的夜晚,一家人都圍在火池四週而睡。年齡比宏一大一些還在上學的小姨們,夏天就帶宏一到山腳下,在小河邊搭起尖頂的草篷,那是宏一記憶中的“夏令營”——在稻田邊抓螞蚱,做成帶醬甜味的小菜拌飯吃;夕陽下山後,小姨們燃起篝火,支上小鍋做醬湯,大家圍坐在一起邊嬉鬧邊吃晚餐。夜深了,數不清的小螢火蟲,在周圍飛來飛去。潺潺的流水聲,幽幽的青草香……飛舞的螢火蟲和夜幕上的星星,小宏一的眼睛看得蒙眬了,漸漸進入夢鄉。和田村有一個小小的電影院。母親曾帶他去看過黑白片的《米老鼠和唐老鴨》。關上燈,屋裏的白墻上,就出現了會動來動去的怪影子,看得小宏一目瞪口呆。
小娃娃對母親的記憶,永遠是兒時印象最深的片段。宏一記憶的都是在故鄉和生母密切相關的“碎片”:
母親總是拉著他的小手,帶他參加三月三“女兒節”,看化裝成古人的小美女;參加五月五“男兒節”,看風中飄舞的鯉魚旗;從塞滿冰塊的桶中舀出一球冰激淩,他甜美地吃著;在男女同浴的溫泉中洗澡;到波濤的大海邊看大船、抓海蟹;還有在村裏讀過小學的母親教他讀平假名的字符,讓他在幼兒時就能讀懂了《桃太郎》《阿裡巴巴和四十大盜》等童話圖書……
小宏一那清貧但是無憂無慮的童年是金色的,小宏一對生母的記憶是那麼親切。

2 “開拓團”生活
1940年的秋末,宏一的父母忙著收拾東西,外祖父一家人的眼神有些異樣。入冬之前,父母帶領著宏一和弟弟駿、妹妹登美子,告別了外祖父母一家人,開始了苦難的歷程。旅途的終點是黑龍江牡丹江市以北的龍爪火車站。後來宏一從母親口中知道:是父親聽信了政府的宣傳,要到一個叫“滿洲國”的地方,參加“開拓團”,開荒種地。一心想讓家裏人生活好一些的父親,沒有聽外公家人的勸告,報了名。
來到這裡,留在宏一記憶之中的,只有冬春的荒原草甸,夏秋的洶湧洪水,還有冬季頻繁聽到的狼嚎聲。記憶中還有農忙時,家裏請了一位當地中國農民做雇工。因為不通語言,家人和雇工只能比劃著交流。父母時常避開“開拓團”裏其他日本人家的耳目,送給雇工一些糧食毛巾肥皂。這位雇工也送過宏一和駿每人一雙做工精緻大小合適的布鞋,還拿過一包食物請宏一一家人吃。那是宏一有生以來第一次吃餃子。以至於幾十年來,每逢吃餃子時,他都會想起這件往事。

3
生死歷程
1945年一開始,“開拓團”裏瀰漫著憂鬱的氣氛。軍方要徵兵了,小村子被派了兩個名額,其中一個就落到宏一父親的頭上。父親走後僅來過一封信,從此杳無音訊,至今在日本仍屬於失蹤人員。父親留給宏一的,只有兩件“遺物”:一件是宏一年逾70才在姨媽處拿到的一張父母帶他和弟弟拍的照片;再一個就是上二年級時正逢雨季發水,宏一摔傷了膝蓋,是父親翻越高崗,蹚水把他背回了家。他腿上的疤痕,已經成為了懷念父恩的“標誌物”了。
8月初的一天,夜裏蘇軍飛機來空襲了。第三天后半夜,鄰居新野叔叔叫起宏一家人説:“黎明就要開始逃難了,趕快做準備!”大家慌作一團。已經沒有了南下的列車,無奈的各家,只能用自己的車馬,帶上生活必需品,倉促南逃。宏一的母親套好牛車,把被褥、糧食和其它必需品裝上車,帶領4個孩子,離開了曾經寄託夢想的“家”,含淚加入逃難的行列。
兩百多人倉促逃難的群體,是個怎樣的隊伍?拉家帶口,攜老扶幼,邊走邊向後張望,要擺脫傳説中追上來的蘇軍部隊,得在林子中穿行,只好丟棄了車輛和較重的物品。不時傳來零星槍炮聲,各種流言,使人們更加惶恐。雨季中河水暴漲,過河時只能靠一條綁在兩岸樹根上的細鐵鏈子。大人們要往返幾次,扛著行李、托舉著孩子,牽著牲口,護送著一家人過去。宏一的母親背著小弟弟秀策,一手抓住鐵鏈,另一手拉著宏一,過到河的中心處,水漫過了宏一的肩部,他身子懸空,感覺要被水吞沒了,幸虧母親拼命拽住他的手腕,扛住了急流,他才與死神擦肩而過。
鄰居丹野家兩歲的小幸子,在一天下午餓死了,那是宏一第一次直面熟人的死亡。為了覓食,有的大人闖進了俄羅斯人的住宅,回來説看到好幾具被日本兵殺害的屍體。大人們還説,最怕的是遇到日本軍隊,傳聞説已有“開拓團”的居民被日本兵集體槍殺或被逼迫自殺。為了充饑,人們不得不殺食寶貴的馬牛。宏一家交出了那頭他最心愛的大牛。大牛拼命掙扎哀號的情景和大牛那雙絕望的眼神,讓他終生難忘。
4
永遠的烙印
倒是遇到中國民間武裝人員後,他們才有了一線生機——沒有被打罵,也沒受到明顯的歧視和侮辱。而最令他們感激不盡的是有了食物。在確認是難民之後,他們被轉交給專門處理日本難民的收容所。難民們用身上的錢和一切可以交換的東西,和當地人換食物。宏一母親為了買食物花光所有藏在身上的存錢,最後不得不用僅剩下的一床棉被,換了兩個玉米麵貼餅子給孩子們充饑。
難民乘運貨列車輾轉到了新京市(長春),住進一所小學校裏。孩子們在附近走動時,宏一發現妹妹登美子突然不見了,不知是走失了還是被人拐走。母親和家人連續找了幾天毫無結果,可憐的登美子就這樣消失了。
禍不單行,幾日後發生了這一家人無法想像的一件事:清晨一睜眼,住所裏空空蕩蕩無聲無息,只剩下宏一一家人了。也許是在逃難人群裏,這樣一個婦女領著4個孩子,成了集體行動的累贅,不得不甩掉。當人們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可能某些人必須做出犧牲。這個平民之家,因為侵略戰爭成為“犧牲者”。這在宏一幼年的心靈裏投下巨大陰影。
11月初,宏一母親帶領3個孩子,混入南下的難民群,又乘載貨列車來到奉天市(瀋陽)。初冬的寒氣襲人,他們進入到南站附近一個日本學校改做的難民所。沒有取暖設備又沒有冬衣的難民們,分成幾堆蜷縮在—起。這裡的待遇很差,偶爾才提供點稀粥,也沒有醫療服務。難民在寒冷、饑餓、疾病中呻吟、掙扎著活命。幾乎每天都有死人被抬出門外。在這樣地獄般的處境裏,母親仍然支撐著病弱的身子外出,到日本人住宅區討要點食物,分給孩子們,而她只是象徵性地嘗嘗而已。宏一因為痢疾,瘦成皮包骨,渾身無力。
一天半夜,一個闖入者來騷擾母親,宏一見狀大喊,秀策也大哭起來,那個人竟然用手持刺刀刺向母親腹部後離去。幾天后的下午,一直處於昏迷狀態的母親,忽然睜開眼睛,嘴唇在動,宏一立刻伸過頭去聽,勉強聽到:“宏—,你……”母親就停止了呼吸。她臉色蠟黃,顴骨突出,眼眶塌下,爬滿蝨子的黑髮猶如染上白霜,她的身下,滲出一片黑色的血跡……在蒙眬的視線裏,弟弟駿睜大眼睛在盯著他,似乎在問哥哥該怎麼辦。秀策還依偎在母親身旁,渾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宏一瞬間進入了無意識狀態,想哭又哭不出來。待有人來把母親抬出門外時,他才雙手抓撓著大哭起來。自從開始逃難以來,母親費盡她全部氣力,想帶領孩子們趕往她心目中的安全地帶。為了實現回到日本的夢想,她把能換的東西全都換成給孩子吃的食物,把自己的衣服披在孩子們身上,討要來的食物幾乎全分給孩子們,自己受凍挨餓。可她還是被罪惡的戰爭奪去了年僅三十幾歲的生命。被饑餓和痢疾折磨得自身難保的宏一,甚至無力爬起來跟著去埋葬地,他至今也不知母親的亡靈飄泊在何方。
失去母親的10歲的宏一,看著身旁兩個需要照顧的弟弟,抑制住了自絕的念頭。當宏一還在沉寂于失去母親的悲痛之際,認領難民孩子的人群裏,一個穿著韓式制服的男子,趁宏一沒注意,突然雙手抓起了小弟弟秀策。宏一使出全身力氣站起來呼喊求助,但他病弱之軀無力爭奪,讓駿去追也沒追上,眼看秀策哭叫著遠去。此後的多年,每見到“秀”字,他就想起幼小的秀策,覺得對不起弟弟,對不起父母親。但是他更詛咒這場給人類,尤其是給無辜平民百姓帶來苦難的侵略戰爭,詛咒發起侵略戰爭的戰犯們!
5
中國父母
就在這對無依無靠饑寒交迫的兄弟走投無路的時候,一個身穿黑棉襖的中國男人來到面前,帶著小哥倆踏上了歸家之路。
男人領他們來到一個大院子裏,領養了駿;另一個壯實男人,領養了宏一。宏一懷著萬分感激之情進到屋裏。一位身材不高的年輕主婦,正邊做飯邊照料一個牙牙學語的女嬰。次日下午,宏一被帶到街裏的浴池洗澡,又換上了女主人連夜縫製出的嶄新的棉衣棉褲,體驗到從地獄到天堂般的巨變。
領養宏一的人叫王殿臣,是河北景縣賈呂村人。他很耐心地教宏一説話寫字。一天,家裏來了一位客人,他微笑著打量宏一,又小聲和主人商談之後宣佈:“你的名字叫王林起,王殿臣是你爸爸,賈鳳朝就是你娘。”從此他就有了中國的父母,成為王家的成員,有了中國名字和戶口,新中國成立後也自然有了中國國籍。多年後他才得知,那人是算命先生,按照中國傳統命理,“算出”王家五行缺木,所以少了男丁。而這個領養來的遺孤,是王氏家族中到來的第一個男孩兒,所以被命名為“林起”。説來也巧,在林起之後,老王家出生了以“林”字排序的近十個男孩。雖是養子,但養父母待林起視如己出,給了他家庭和家族老大的待遇。
弟弟駿沒有享受到這樣的福氣。春節後的一個早晨,他突然死亡。裹在席子裏的遺體,被放置在大門洞裏。駿的離去讓林起痛苦萬分。可惡的侵華戰爭,讓他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弟弟妹妹,失去了家,失去了一切,最終變為渡部家的孤兒。
1948年秋天,林起一家人來到北平,在豐臺正陽大街安頓下來。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上了小學的林起,成為第一批少先隊隊員,後來還戴上“三道杠”,成了大隊旗手。
1953年夏天,18歲的林起在小學畢業會考中考了第一名。他想為家庭分憂,及早參加工作。老師到家裏做工作,父母堅決支持,讓他到北京市第十二中學繼續求學。1957年夏,林起經過十幾天腹痛治療無效,突然疼痛難忍。父親立刻背起他跑向二百米開外的公交車站去了醫院。診斷是闌尾炎轉重症腹膜炎,做了三次手術。父親歇業守護他。這是中國父母又一次挽救他的生命。看病的費用花去了家中積蓄的三分之二,林起擅自決定棄學就業。
他成了籌建中的北京汽輪機廠的一名磨工,見證參與了這個國家重點發電設備製造廠的建設和發展。後來,這個廠併入了北京重型電機廠。在廠裏決定自製大型機床時,王林起承擔了12米龍門刨床的大部件加工任務。他在這個廠一直幹到退休。
1960年12月7日夜,正在車間上夜班的王林起接到值班員通知,他的養父突然過世了。極度悲痛的王林起和弟弟妹妹們一起料理了養父的後事。事畢,他想起幾天前養父罕見地用老家方言和他説的話:“我挺想到你日本老家看看,可説不定去不成了。沒能供你上大學,挺對不住你的。”這應當是養父對他的叮囑吧?一個是學習成才,一個是回鄉尋根。
6
回鄉之路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很多日本戰爭遺孤,都通過外交途徑回到日本。王林起卻沒動念頭。因為他早已説不清自己在日本的情況了。
幾年以後,還是老同學吳樹仁提醒他,應當完成養父的遺願。他用漢字給和田村村長寫了一封信。回信是日文。技術科長但功溥請人幫忙翻譯了。信中告訴他祖父和外祖父家都有健在的親戚,可以直接與他們通信聯繫。於是他分別給姑母和姨母們寫信。幾經週折,他先後收到姑母和三位姨母的信。大姨母和玲子錶妹還在信封裏放進一萬日元,讓他給養母買禮物。收到隔海的敬意,養母很高興。這使得早已決心不回日本的王林起,産生了不能拒絕長輩親人的願望,有了去日本探親的念頭。
歷經一系列複雜的程式,兩年後,他辦妥了一切手續,可以成行了。臨行前,養母握著他的手説:“你對我們家的義務已盡完了,放心走吧,不用回來了。”林起明確地告訴養母:“我一定會回來的。”在北京重型電機廠,廠長孫濟民和黨委書記周鶴良特批按出國人員待遇,給王林起按公派出國的標準,發放了五百元的置裝費。周鶴良説:“一個深受侵華戰爭之害的日本遺孤,一個在北重廠工作多年的中國公民,置辦新裝是為了中國人的臉面。”
1981年5月20日上午,家人、單位領導和很多同事朋友,到機場為他送行。
在日本,王林起回到他出生的小山村。時光流逝,社會發展,很多地方變化了,但老屋、山川河流依然沒有變。他漸漸地找回了5歲以前在這裡生活的碎片,也想起了日語和日文,甚至想起來母親背著他時唱的童謠:“春天來了/春天來了/來到山裏/來到田裏/也來到原野裏。 花開了/花開了/開到山裏/開到田裏/也開到原野裏……”他傳奇般地回憶起在生母身邊的很多情景。這在日本遺孤中很少見。為此,他受到日本媒體的關注和政界經濟界人士的重視。“在中國,我只是一個普通公民,認識的只限于周圍一些人;到了日本,我倒成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了。為此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民間信使,為中日工業技術界溝通信息。還要為遺孤和他們的中方養父母呼籲。”
一年零兩個月之後,他毅然回到北京,回到他中國媽媽的身邊。令他驚訝的是:回來後,人事勞資部門照發了他赴日期間的全部基本工資。
此後,王林起在多次回故鄉看望親友的同時,對中日之間的民間交往也盡了個人的力量。他向日本厚生勞動省提出,希望日本政府或民間團體,向救助養育了日本孤兒的中國養父母表示感謝,並給予一定的補償。2011年,時任日本駐華大使的丹羽宇一郎先生曾為在京的4位“遺孤”家庭舉辦午餐會,王林起又向大使當面提出了這個心願。大使先後到山東、東北等地走訪了養父母和家屬們。2011年6月1日,丹羽大使在日本使館舉行儀式,向在京遺孤的幾位養父母致謝。丹羽大使鞠躬施禮,親手把日本政府的感謝狀呈交給王林起的中國媽媽賈鳳朝。年逾90歲、因腦血栓喪失語言功能的養母高興地笑了。次日,中國的《環球新聞網》、日本《東京新聞》等報道了此事。
日本遺孤渡部宏一在短期內神奇地從記憶中搜尋出童年的線索,終於找回自己出生的故土,被日本多家媒體稱為具有“傳奇色彩”。這也感動了王林起在中國的老朋友們,大家都建議他寫書。不是為了他和日本的親人,而是用他親歷的戰爭苦難和一個遺孤在新中國的生活,告訴人們:法西斯戰爭的受害者,不僅僅是被侵略的國家和人民。侵略者本國的人民,也深受其害。
歷時一年,幾易其稿,最近,王林起和一些老同事小聚,他宣佈:“《我在中國的75年——二戰日本遺孤自述》,已經和西苑出版社簽約,即將正式出版。這是為了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我把這本書獻給我的兩個母親——生養我的日本母親和養育我的中國母親。日本和中國,永遠是我心中的兩個祖國。”
新聞推薦
- 全國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閉幕 習近平等出席2026-03-11
- 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發言人:堅決粉碎“台獨”分裂和外部干涉圖謀2026-03-11
- 外交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歷史2026-03-11
- 台灣代表團熱議生態環境法典草案 以法治之力共繪兩岸美好藍圖2026-03-11
- 許可慰:在大陸 愛拼真的能贏!2026-03-11
- 前兩月兩岸進出口貿易額同比增長21.7%2026-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