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把日子過成詩
| 編輯: 陳豪 | 時間: 2014-11-28 15:52:26 | 來源: 光明日報 |
【人物·大家】
作者:李琭璐
謝冕先生今年82歲了。
先生老了,親友們總是勸他好好保養,要活到一百歲。聽到這些善意的祝願,謝冕心裏很不是滋味。不是懼老,而是他越來越感覺到“壽”字背後的空虛與乏味。如果精神與肉體能夠同步衰老,那是一種值得欣慰的和諧,而先生不是這樣。
頤養天年的日子謝冕過不來。養花養草、玩鳥遛狗他不感興趣,下棋打牌更不會,甚至不辦壽,過節、過年均從簡。

在《我的西郊生活》裏,謝冕寫下這樣一段話:“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隨心所欲,不忍過於苦了自己。唯有這夜闌人靜之後的寫作才是愜意的,也説得上是‘認真’的。”
對於這種“刻板”的生活,謝冕有過自責。但是沒辦法,既然“嫁”給詩歌,就靠詩歌活命。
盛夏時分,我試探性地撥通了謝冕家的電話,説明採訪意圖,沒想到他很痛快地答應了,甚至主動問,你哪天有時間呢?如此大師,如此謙和,不覺讓我心裏一暖。
採訪路上遇到一小盆火鶴,翠綠的葉,火紅的掌,心中一動,後來為先生買下遞到家中。花雖輕,先生依然欣喜地發短信給我:“花很美,老師很喜歡,謝謝你。”
那日,夫人陳素琰正要出門,看有來客,忙走出屋外表示歡迎,茶几上的龍井茶,已經泡得很釅了。這對頭髮雪白、相濡以沫的夫妻,已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
北京昌平北七家,一片普通的歐式別墅群,謝冕一如既往的低調。問周圍鄰居,竟然不知道還有這樣一位大家住在隔壁。有時先生下樓散步,被人認出,總是笑著説,不是的,不是的。
房間簡樸至極。依然是水泥地,客廳墻壁只有一挂鐘,再無更多裝飾。陽臺上擺滿了植物,一大株綠蘿挺拔蒼勁,門口的書堆得有一米多高,斜斜地靠在墻邊,先生有些不好意思:“書太多,有些亂。”
年至耄耋,謝冕的晚年作品更多偏向於詩歌評論,少了曾經的恬淡詩意,多了內心的情緒萬千。憤怒、激烈、歡樂與憂愁……人愈年長,情愈濃烈。
而謝冕也一生警醒,始終沒有高高在上。是大師,更是草芥。
詩歌·探索
夏日的暖風搜索著地面,刮不到任何東西,早些時間落得滿地的玉蘭花,早已都被清潔工清走。紅磚墻,水泥門汀,銹澀的自行車在別墅樓前擺成一排。
那日,去謝冕家是暴雨來臨前的天氣,遠處的天並不晴朗。也可能是我有把現實文藝化的潛意識,故意要沉溺于一種陳舊的環境裏,又孤獨又安定。
讀過謝冕的詩歌與評論,我總覺得他是孤獨的,冒昧地這樣想。
這一次,我請先生敘説個人歷史,企望有好的運氣——願他是善談的,不用我提問,便可滔滔不絕。但謝冕不是那樣的人,説出來的都是片語微光。

我幾乎沒法跟先生展開辯論,他駁你一遍之後,你想誘他多説些而故意説反話,他卻毫不接招:“你這樣想,也可以,也有你的道理。”
我們不斷地陷入僵局,我思路受阻,尷尬,幹著急,謝冕卻保持著一個樂呵呵的固定姿勢,眼睛望著一摞書,像是進入另外一個時空。
謝冕自幼喜歡詩,有古典詩,也有新詩。古典詩好像一座高山,謝冕很嚮往,但是心嚮往之而不能及;新詩是身邊的,好像朋友,有一種親近感。
“我從少年時代就是詩歌少年,很喜歡詩,而且也學著寫。年紀大了對成熟的人生回顧起來,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幼稚,那麼天真,居然寫了那麼多。”謝冕從新詩中懂得了一個道理,即詩歌與人的情感、內心世界是有關係的,特別是和自由的內心世界、一種無拘束的情感是有關係的。
詩歌是和心靈非常接近的一個文體。受到“五四”新文學及新詩革命的一些前輩影響,謝冕看到他們能夠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表達得那麼充分,那麼無拘無束,“這個境界實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學”。
那時,謝冕知道胡適,知道郭沫若,還有後來出現的一些新詩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覺得他們的表達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這樣接近了詩,學習詩,夢想做詩人。”
1948年,散文《公園之秋》發表于福州出版的《中央日報》。這是謝冕第一次發表文學作品。文章寫道:“楓葉紅似榴火,我不想做一首華麗的讚美詩,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難大眾的血跡;他們,這批可憐的被獻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臨之前,他們被黑夜之魔奪取了。血,斑斑地染在楓樹葉子上。”
謝冕17歲時,新中國成立。他自己也投身革命,穿上軍裝,自願而真誠,幾乎沒有任何世俗考慮,就是告別舊中國,建設新中國。
當時,謝冕由少年轉入青年,雖然他仍在寫詩,但總覺得所寫的並不是自己想寫的,“我是按照一種理念、一種號召來寫的,那不是真實的我,而且‘我’也消失了,‘我’的消失是最嚴重的一個事件,詩不能表達一個活生生的、有活潑的思想和情感的我,那是最可怕的一個事情了”。
謝冕最終放棄了詩歌理想。
20世紀50年代,謝冕與其他5位作者共同寫成了《回顧一次寫作——新詩發展概況》,“那是很複雜的一個産物,也可以説是少年無知,那對詩歌歷史是歪曲的寫作、歪曲的表達。那也是歷史的産物,同時也是充滿了內心矛盾的産物,現在我把它保留下來了。”謝冕認為,這部著作的主導思想是不對的,將詩歌分為革命詩歌、不革命詩歌、反革命詩歌,現實主義詩歌、反現實主義詩歌,這些觀念是有毛病的。“當時隱隱地感覺到這是錯的,但又不敢説不對。”
謝冕一直盼望著新詩走出絕路,讓青年看到希望,看到新詩能夠和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內心世界結合得很好。
20世紀70年代中期,“文革”結束前,遇到了現在的朦朧詩,後來又遇到了那些被流放詩人的“地下寫作”,謝冕覺得他看到了希望:“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這就是我當時的心情。我能夠毫不猶豫地站在新詩潮的潮流中,來表達我自己的感受,這就是我所盼望的詩歌,我所想念的詩歌,現在終於回來了。”
“新詩面臨著挑戰,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人們由鄙棄幫腔幫調的偽善的詩,進而不滿足於內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詩,詩集的印數在猛跌,詩人在苦悶。與此同時,一些老詩人試圖作出從內容到形式的新的突破,一批新詩人在崛起,他們不拘一格,大膽吸收西方現代詩歌的某些表現方式,寫出了一些‘古怪’的詩篇。越來越多的‘背離’詩歌傳統的跡象的出現,迫使我們作出切乎實際的判斷和抉擇。我們不必為此不安,我們應當學會適應這一狀況,並把它引向促進新詩健康發展的路上去。”這是1980年5月7日,謝冕在《光明日報》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引發了關於新詩潮的熱烈討論。
對於別人的圍攻,謝冕不作申辯,朦朧詩論爭的對手都是大牌詩人和身居要位的評論家,可他從沒有寫過一篇答辯文章。他保持沉默,這是一種境界。
謝冕自稱“反季節寫作”,其專著也是一反常態在賓館裏寫而不是在圖書館寫。他記憶力超常,才華橫溢,富有感染力的爽朗笑聲時時濺落。
那天,陽光很好,我們很多時候都是默默相對,間或閒言碎語地笑一下,心情鬆弛、眼神渙散,分別進入一種自顧自的狀態,卻又不覺得無禮。
客廳兼會客室不足30平方米,坐了兩個小時之後,謝冕突然問我:“你讀過《詩探索》雜誌嗎?”那是他從1984年辦起來的雜誌,銷量不大,更不賺錢,但做得有聲有色,雖沒熱賣,卻也被眾多詩歌愛好者掛念。
這座城市並不缺乏詩歌的氛圍和熱情,而詩歌用更大的熱情點燃了謝冕。“我們只不過在一個真空地帶,做了別人沒有做的事情。”
當然,世界上還是會有一些讓謝冕特別震動的事情。“唉,對了,我想説個事情給你聽。”他很鄭重地説起在網上看到的一則新聞,“廣西玉林還有狗肉節啊!那些動物多無辜。”先生的眼睛瞪得老大。
師道·呵護
“儘量不要打擾我的學生吧,他們太忙。”當我提出要側面採訪他的學生時,謝冕特意叮囑。
謝冕的學生,大多活躍在當今學術界。
學生張志忠説,謝先生尤為可貴的,是他對青年詩人的全力扶持,30餘年間,他為青年詩人撰評作序,不遺餘力,這在當代詩評家中可以説是為數不多。“早些年間和先生交談,我曾經勸他,不用這樣來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個來訪者、來信者,這樣的雜事太多,沉不下心來,會妨礙做更重要的學術研究。”
“不能把青年人擋在門外啊。”那些來自遠方的訪客和書信,在謝冕這裡都得到了熱情的迴響,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還是詩人們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過一面之緣,還是素不相識,在他這裡都不會碰壁。
甚至還有這樣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詩人去世,他的哥哥為了滿足逝者的心願,將其詩歌編成集子,到謝冕這裡求序,他欣然允諾。
在謝冕這裡,與青年詩人的交流,並無等級差序,首先是一種情感和詩性的撞擊。就像魯迅當年,為那麼多的青年作家寫序,稱讚他們的生命熱力。而被魯迅評價過的青年作家,有許多今日已經湮沒無聞,但是,文學評論畢竟不是選擇“績優股”和“潛力股”進行投資,扶植新人,推薦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為新人新作推波助瀾,為當下文壇留下參差錯落的風景,這才是真正有見識、有熱情的大家風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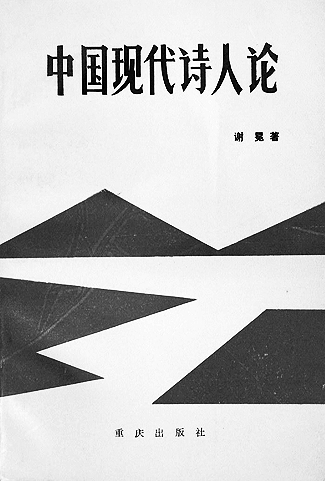
學生們常笑謝冕是“守財奴”,每次上北大取信件,總會拿一大包回家,看過後整整齊齊地擺放一旁,不捨得丟掉。“反觀諸己,若不是當年先生不棄草芥,把稚拙愚鈍的我收留在門下,耐心提點,對先生來説,不過是少了一個來自古城太原的弟子而已,而對我自己,人生的軌跡可能就會産生很大的改變,學術之路會走得異常艱難吧。”謝冕惜才,張志忠上學時常在先生家吃飯,受到很大關照。
“老孟”,這是謝冕對學生孟繁華的稱呼,二人相識32年。多年前,在北大有個批評家週末,開始前,謝冕隨意自如,談笑風生,學生們則自在率性,書生意氣,師生間的談話海闊天空。一旦正式開始的時間到了,頓時安靜,“老孟還沒來?等等老孟,他説來的。”謝冕的話音剛落,孟繁華就氣喘吁吁地進來,一副莊嚴而厚重的樣子。謝冕笑著説:“老孟來了,大師來了,我們開始吧!”孟繁華朗朗大笑,算是對先生的回答。
謝冕對待學生一向寬厚溫和,但也有發火之時。1992年,謝冕讓孟繁華第二天陪他一起買《新青年》雜誌影印版,但當天從意大利使館來了位學習當代文學的學生,孟繁華便把先生交代的事情忘了。“先生當時很生氣,教育我要對他人的事情言而有信,要有時間觀念。”事後,孟繁華騎車又去買了一套雜誌,從此再沒爽約過。
高秀芹,謝冕最小的學生。她讀博士時,正值謝冕63歲,畢業後與先生交往甚多,一些詩歌活動都會見面,她認為先生沒有老過,保持了最好的活力,堪稱“行走的詩人”。“他能看到學生的優點,畢業時不限定我們的論文題目,但要求學生從宏觀的角度敘述細節。”
畢業後,學生們雖然在不同領域發展,但謝冕總是惦記,時不時就聚一下。在高秀芹眼中,謝冕本身就是一首詩,“與他在一起,我們都是老的,他是詩歌的孩子。他一生都在呵護著詩。”謝冕為詩歌奔走,不喜歡説不,而且都會給予最熾熱的關愛。各地的詩歌活動,但凡需要他,從不推脫。
“讀書不一定非要有個目的,讀書本身就是目的。”謝冕常開玩笑説,自己好讀書,但不求甚解,“我翻得不夠,到了這個歲數,應該多到圖書館看書。”
人的知識面是不斷翻書翻出來的,讓謝冕得意的是,他曾經讀過一個麵包車的書,記過大量筆記,還將感興趣的內容裝訂成冊,隨時翻閱。因為如果不閱讀作品,在新詩領域就不配有發言權。
讀過許多書,但謝冕並不想寫專門的文章來論述自己的觀點,“我寫了也沒人理嘛。”話雖這樣説,但他是不會去做“錦上添花”的學問的。
謝冕常常會引用詩人濟慈的一句墓誌銘:“這裡躺著一個人,他把名字寫在水上。”像他這樣的人,幾無佔有欲,對於知識、名氣、權力,甚至於“來自他者的認可”等抽象的東西,全都無欲無索。
這樣一個大熱天,謝冕在家裏完完整整地穿戴著乾淨的襯衫、鞋,手腕上還戴了手錶,一副要外出的樣子,他坐下來之後,褲腿縮了上去,露出深藍色襪子,腳背上有一個大洞。
謝冕在北大暢春園的家,書籍幾乎佔據了所有空間,另有一尊拜倫雕像。這樣一來,他的房間就顯得格外擁擠,外人來了總會一不小心就碰這碰那。所以,每逢送客,他都要謹慎地提醒:“小心腳下!”
性情·自由
“你沒有經歷過‘文革’,我替你可惜。”謝冕對我説。我驚訝地笑出來:“為什麼?幾乎每個經歷過‘文革’的人都咒罵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應該擁有不同的體驗。”我無法接受:“一個從事精神研究的人當然最好有豐富的經歷,但從生活層面來説,普通個體追求的還是幸福吧?”
謝冕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為太震驚,之後我多次向別人轉述他的這個觀點,經歷或沒經歷過“文革”的人都不認同:“怎麼這麼想?我完全就不想經歷‘文革’!”
“我害怕經歷那個年代。”我對謝冕説,“我很難保證自己能在運動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輩子都要活在自責的痛苦中。”
謝冕笑一下:“不一定,現在有多少人在懺悔呢?”
我一直困惑:為什麼那麼多有思想的人在某個歷史時期,曾經集體地發生了那麼大的人格變化?“歷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體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個人意志的結果,被帶入群體的個人總是受無意識人格的支配。”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給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釋,熱情又單純的人很難不被捲入集體情感,況且那曾經是一種“幸福感”。
“你們上學的時候,正是戰爭時期,不會害怕嗎?”“不會,我覺得很幸福。”那時候,包括謝冕在內的絕大多數年輕人都堅信: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謝冕説,一個人感到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一個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
現在,謝冕已經活了82年。他説:“無法相信未來的世界就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但不往前走一步,怎麼會知道結果?”
“謝門”有個“餡餅大賽”,固定的比賽地點是昌平太陽城裏的餡餅店,而餡料就是普通的豬肉大蔥,活動迄今已辦了3年。謝冕一人能吃七八個,但有個女學生能吃十個。今年改成了“包子大賽”,更是有學生吃下了六個大包子。“在那個氛圍下,有什麼比吃餡餅更重要的事呢?”謝冕側著頭,笑瞇瞇地問我。
謝冕喜歡用粗糙的生活方式來表現鮮活的生命力,年紀越來越大,他卻越來越饞酒,常常在飯桌上觥籌交錯,紅酒白酒啤酒混著喝。
每逢大年初六或初七,學生張頤武會到謝冕家拜年,聊過之後,便會把先生和師母從昌平的家中接出,先去北大理髮,再去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維蘭西餐廳吃飯,“謝先生對牛排和咖啡等西餐情有獨鍾。”20世紀80年代中期,張頤武還是學生時,謝冕就曾多次帶他去吃西餐,“現在是顛倒過來了。”
中國作家協會研究員李朝全在《飄落在燕園的一粒種子》一文中寫道:“謝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具有濃郁的詩人氣質。這大概是他的詩歌為何如此文采斐然的重要原因吧。跨進他的家門,首先聽到的便是一片仿佛從遙遠的叢林中傳來的鳥兒的喧鬧聲,這是先生養的小鳥在歡迎客人呢。每當此時,他便會走到鳥籠前,故意做出教訓小孩的樣子,高聲呵斥:‘這樣高聲地叫,真是個人來瘋。’那些美麗的小鳥,説不清究竟有多少只,竟都害羞似的噤了聲,低下頭去,裝作啄食小米或是水罐裏的水,眼睛卻不時偷偷抬起去溜先生一眼。鳥兒們都不長記性,或許是受先生的感染生性樂觀開朗,等到下次客人來時,小鳥們依然如我。謝先生還是像往常一樣,當著客人的面高聲地訓斥它們,小鳥們依舊裝作噤了聲,埋頭去偷聽主人與客人們的談話。”
“我是想不通,有些老年人為了多活幾年,付出的代價是這個不吃那個不喝。我經常鍛鍊,我什麼都吃,活得好好的。”謝冕洗衣服從不用洗衣機,夫人與他各洗各的,“就愛洗衣服。”先生笑著打趣。
謝冕這樣總結自己:“一點自由主義,一點唯心主義,加一點唯物主義。”回顧起來,他在北大度過了數年歲月,是他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原因是:自由。
謝冕崇尚自由。
2008年去杭州,看到碧波湖水,謝冕興奮得繞湖跑了一圈,是性情中人;每一次詩歌研討會發言,謝冕總要寫出稿子,開會結束後,稿子就可拿去發表,是虛心之人;謝冕興趣廣泛,出差每到一個景點,都會拿著筆和本詳盡記錄,勤奮發問,是心細之人;謝冕不搞特權,早年出差,活動主辦方考慮他年齡大,特意買了軟臥,但他自己又換成了硬臥,老友劉福春説,不同年齡的人與謝冕在一起都會快樂至極,是低調之人;謝冕謙虛謹慎,一次開會,幾位年輕人批評詩歌界之怪現象,他笑著回應:“我不能免俗。”是大度之人。
在認真與隨和中,在自由與原則裏,在悲觀與樂觀間,謝冕保持了很好的平衡。除去寫作,他還喜歡吃,到任何地方的餐館習慣抄菜譜。
北大東門的紅辣子飯館,每逢謝冕就餐,服務員總會甜甜地喊一聲:謝爺爺來了。先生很高興,邀其坐過來一起聊聊,這種既溫暖又有人情味的生活讓謝冕很是陶醉。
老友洪子誠説,謝冕這20多年來,為學術,為新詩,為新詩的當代變革,為朋友和年輕人費了那麼多心血,做了那麼多事情,自然獲得許多人的愛戴、尊敬,但相信他也不會沒有體驗過“世態炎涼”。
十多年前,洪子誠和謝冕到南方的一所大學去訪問,那裏的領導奉他們為上賓。再過幾年,又到那所學校開學術會議,可能覺得他已經“過氣”,也沒有佔據什麼政治、學術的資源和權力,對他就換了一副面孔:雖客氣,但明顯將他冷落在一旁,而改為熱捧那些掌握著“資源”的人。
因為親眼見到這樣鮮明的冷暖對比,洪子誠不禁忿忿然。但謝冕好像並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地認真參加會議,認真寫好發言稿,認真聽同行的發言,仍一如既往和朋友談天,吃飯仍然胃口很好,仍然將快樂傳染給周圍的人。“我有點慚愧,他也許不像我這樣的狹隘。”
在《北京大學當代學者墨蹟選》中,收有謝冕的墨蹟。先生寫的是培根的語錄:“幸福所生的德性是節制,厄運所生的德性是堅忍,奇跡多是在厄運中出現的。”——這應該是他所欣賞、甚至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學”了。
以“節制”和“堅忍”來概括謝冕性格中的重要方面,應該是恰當的。他經歷厄運,對待厄運他取的態度是堅忍;他對自己能夠獨自承擔擁有信心,他也不願意給別人帶來麻煩和負擔。在他的生活中,又確有許多幸福。他懂得幸福的價值,知道珍惜。但從不誇張這種幸福,不得意忘形,不以幸福自傲和傲人,也樂意于將幸福、快樂與朋友甚至與看來不相干的人分享。
下午5點,採訪結束。謝冕起身送我到門口,又馬上走回去抬眼看看表,囁嚅著:“素琰怎麼還沒回來?”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相關新聞
新聞推薦
- 習近平春節前夕慰問部隊 向全體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武警部隊官兵軍隊文職人員預備役人員和民兵致以新春祝福2026-02-13
- 王毅:做到“五個共同”,深化中匈友誼,拓展互利合作2026-02-13
- 外交部:“倚外謀獨”是蚍蜉撼樹 註定失敗2026-02-13
- 全球看春晚!總臺“春晚序曲”俄羅斯專場活動在莫斯科舉行2026-02-13
- 國際銳評丨從“圍觀”到“融入”,感知馬年春節裏的中國文化密碼2026-02-13
- “兩岸一家親 真情助企行”——2026年迎新春臺企特色産品展銷會開展2026-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