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為中國共産黨歷史展覽館漆壁畫《長城頌》(部分),主創程向軍。

圖片從上至下依次為歌劇《白毛女》(郭蘭英主演)、京劇《楊靖宇》、話劇《四世同堂》劇照。
資料圖片

來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的雕塑《我要去延安》,材質為玻璃鋼倣銅,主創陳輝,製作團隊為朱全俊、劉志、王成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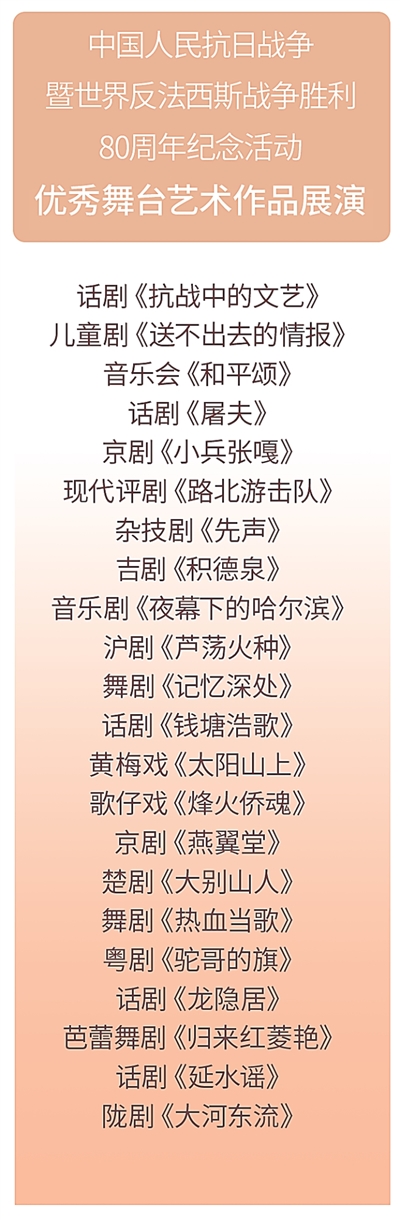
山河作舞臺 發出奮起的雄音
王 瑨
老舍先生筆下《四世同堂》的祁老太爺,用米缸堵住了家門,卻堵不住侵略者的鐵蹄。
一個民族在劇痛中驚醒。
九一八事變後,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迅即首演,從此成為眾多演出的首選劇目。直至抗戰結束,它如流動的抗戰火炬,點燃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
盧溝橋事變僅過去一個月,三幕劇《保衛盧溝橋》上演,臺上唱《義勇軍進行曲》,台下跟著唱。中國戲劇人吹響了時代的號角——“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演員四億人,戰線一萬里,全球作觀眾,看我大史戲!”烽煙為幕,大地為席,每一處舞臺都凝結著四萬萬人的吼聲,“我們願以鮮血向前”。
憤怒,奮起!抗戰舞臺喚起了“我們”,喚醒著個體生命體驗與民族命運的深刻連接。
那是切膚的血淚之痛。河北白洋淀,戰士看著河北梆子《血淚仇》入了神,老鄉看戲流著淚,他們沒有忘記,千里堤上,灑著戰友的鮮血。那是感同身受的痛。街頭劇《淪亡以後》疾呼:“李全哥和桂英的悲哀,是你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悲哀,同時也可以説是我們全中國青年的悲哀!”街頭的日常空間成為情感共振的劇場,將一個個“我”聚合成同仇敵愾的“我們”。
不屈,不畏!抗戰舞臺發出了歷史深處的民族吶喊。
郭沫若將抗戰時人們心頭的激憤,化為話劇《屈原》詩般的語言,“眼淚有什麼用呀?我們只有雷霆,只有閃電,只有風暴,我們沒有拖泥帶水的雨!”梅蘭芳身扎大靠,擂起戰鼓,在京劇《抗金兵》中激憤唱道:“恨金兵亂中華強兵壓境,我全家同報國甘願犧牲。”捨生忘死的民族血性,萬難不屈的民族精神,熔鑄成一代代中國人心中的長城,根脈永固,何等壯闊。
“壯絕神州戲劇兵,浩歌聲裏請長纓。”澎湃的愛國激情,充沛的革命熱忱,縱情而來,信筆成篇,抗戰戲劇創作速度之快、數量之多、傳播之廣,成就斐然。
當我們回望蓬勃發展的抗戰時期戲劇,不難發現,它的強力支撐,來源於一支從“小我”走向“大我”、從“小魯藝”走向“大魯藝”的隊伍,來源於戲劇與現實持續的深刻互動。
延安的鄉親們一聽説“魯藝秧歌到咱村”,便為演劇隊員們準備了難得吃上一回的白麵饸饹,“十里路上迎親人”。
這是怎樣令人難忘的歲月?郭蘭英曾對我説,她一輩子演不夠的、最愛的還是歌劇《白毛女》,“《白毛女》改變了我的人生,帶我走上革命道路,徹底改變了我對藝術的理解。”12歲加入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兒童劇團的田華堅定地説,“我沒離開時代、沒離開生活、沒離開人民,所以自己這顆螺絲釘還沒有完全老化。”“人民藝術家”在抗戰烽火中淬煉著自身,在人民中找到了文藝真正的生命力。
一方舞臺,定格著昂然的英雄身姿,映照著中華民族的浩然國風。聽!抗戰街頭的血誓與怒吼,還有我們共同的心跳。看!今日舞臺的抗戰創作,都是血脈的複寫。那依然響亮的聲聲號角,鼓舞著我們為民族偉大復興奮鬥到底。
正義必勝!和平必勝!人民必勝!任時光流逝,中華大地上英雄的人和事、氣與魂,永遠感動著我們、激勵著我們,被一代代人銘記。
山河舞臺,風光無限。正因,“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正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
戲劇是我們的刀槍
郝 戎
1938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魯藝)誕生。民族危亡之際,集結在魯藝的文藝戰士,以戲劇為武器,用《白毛女》《兄妹開荒》《農村曲》《流寇隊長》《軍民進行曲》《松花江上》《周子山》等作品,記錄抗戰歷史的鮮活肌理、塑造平民英雄的不朽群像、凝聚全民抗戰的磅薄力量。
魯藝的戲劇創作,以紮根現實為核心:年輕藝術家背著畫板、帶著劇本,深入南泥灣的墾荒現場、前線的戰壕陣地,把軍民的真實生活、所思所想搬上舞臺。1943年創作的秧歌劇《兄妹開荒》便是典型:劇中再現了邊區“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産運動,沒有戰爭場面,只有田埂間的對話、勞作中的歡歌,卻精準捕捉了抗戰時期每個人都是參與者的歷史本質。觀眾從劇中兄妹的身影裏看到自己,從唱詞裏讀懂抗戰與己相關。《兄妹開荒》帶動了秧歌劇的創作,推進了延安抗戰劇的進展。
魯藝的戲劇用故事勾勒出“普通人如何成為英雄”的軌跡。1945年,大型新歌劇《白毛女》將這一創作理念推向巔峰。《白毛女》這部從“小魯藝”走向“大魯藝”的新歌劇,劇本題材源自河北民間“白毛仙姑”的傳説。創作者賦予主角喜兒深刻的時代內涵:她的“反抗”不是突然的覺醒,而是逐漸認清真理。劇中沒有“超能力英雄”,只有喜兒從“躲山”到“下山”的蛻變,以及趙大叔、村民們從“沉默”到“團結討還公道”的集體覺醒,他們從苦難中來,向光明走去。觀眾看到喜兒,就像看到鄰家受欺負的姑娘;看到村民們抱團反抗,便明白什麼是英雄與勇氣。演出時,有戰士怒拔槍想打“黃世仁”,有老農抹著淚説“喜兒的苦就是我們的苦”,足以見得,平民英雄群像已成為喚醒民族反抗意識的象徵。
抗戰時期,文藝最重要的使命是“團結人”——魯藝的戲劇便以情感為紐帶,將臺上台下的力量擰成一股繩。
舞臺就是戰場,戲劇就是我們的刀槍。這些作品用“共情”激發行動:《白毛女》中,喜兒的苦難讓大家看清“抗戰不僅是打鬼子,更是為了推翻吃人的舊世界”;《兄妹開荒》裏,兄妹的樂觀與幹勁,讓“苦中作樂搞生産”成為軍民的共同信念。魯藝劇團還常背著道具箱,到前線戰壕、農村土臺演出:戰士們看完《白毛女》,紛紛寫下“為喜兒報仇、為民族雪恨”的請戰書;農民們看完《兄妹開荒》,主動多交公糧、報名參軍。臺上的故事與台下的生活相呼應——這便是戲劇的力量。
1953年,延安魯藝首任副院長沙可夫被任命為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黨委書記。他為魯藝創作的院歌中這樣寫道:“我們是藝術工作者,我們是抗日的戰士,用藝術做我們的武器,用藝術做我們的武器。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爭取中國解放獨立,奮鬥到底……”
抗戰勝利八十載,延安魯藝的戲劇早已超越“藝術作品”,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記憶。它們用舞臺記錄的,是民族抗爭的真實足跡;用角色塑造的,是平民英雄的不朽精神;用情感凝聚的,是“萬眾一心”的民族底色。
(作者為中央戲劇學院院長)
以文藝之力塑造英雄
田沁鑫
從改編蕭紅小説《生死場》的同名話劇,到改編老舍先生小説《四世同堂》的同名話劇,再到文獻話劇《抗戰中的文藝》,多年來,我們努力用文藝作品傳遞偉大抗戰精神,以文藝之力塑造英雄、凝聚力量。
魯迅先生為小説《生死場》作序:“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年輕的作家蕭紅以散文化的筆觸,描述了“九一八”前後的哈爾濱近郊,遭到日軍鐵蹄踐踏的村民從麻木到決心抗日的歷程。話劇《生死場》延續原著對生老病死主題的探討,沿用村民抗日的憤慨情節。
我清楚記得1999年話劇首演時觀眾的熱烈掌聲。劇中,自發抗日的後生成業,挺著脊梁,舉著槍喊:“若是不抗日,天殺我、槍殺我,槍子可是有靈有聖,有眼睛的啊!”演員們演繹的真情實感令觀眾信服。話劇《生死場》懷著對民族命運的反思、對民族主體精神的探尋、對民族自省意識的呼喚,跨越了時空,首演至今,依然帶領觀眾共同致敬這群平民英雄!
2010年,由老舍先生的長篇小説《四世同堂》改編而成的話劇首演。改編初期,我不明白,老舍先生為何把一個面貌模糊的“老實人”祁瑞宣作為主角?寫戲、排戲是學習、成長的過程,我的心境隨劇情走過了8年——衚同裏的祁家、冠家、錢家三家及街坊老少幾十口人,個人命運伴隨國家命運起伏跌宕。
我看向劇中的眾生百態,看他們迥異的人生選擇。我似乎明白了,這是老舍先生用心良苦的安排:讓不夠“英雄”的祁瑞宣成為主角。因為祁瑞宣就是我們。我們老實本分,不像冠曉荷那般活得光鮮亮麗,也沒能像祁瑞全那樣出城抗日。我們有家庭責任,照顧老幼;我們心有底線,不做漢奸;我們憂思國家,承受苦難——我們堅信,堅信民族的不屈;我們堅持,堅持到抗日戰爭最後的勝利!話劇《四世同堂》是一部講堅守的“平民史詩”,史詩裏的平民英雄,恰似祁瑞宣一樣平凡而偉大的中國人民。
2022年,我們推出首部文獻話劇《抗戰中的文藝》,展現魯迅、郭沫若、茅盾等眾多抗戰時期的文藝名家的求索奮鬥、家國情懷。劇中將影像和演員的舞臺表演相結合,用類似環境戲劇的方式,將一個個鮮活的英雄人物形象呈現在觀眾面前。2023年,我們將話劇升級打造為戲劇電影,今年,我們推出“CNT現場”高清展映季,《抗戰中的文藝》以高清影像的形式,讓抗戰精神在科技賦能下得到更廣泛的傳播。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的歷史時刻,用文藝作品致敬先烈、致敬抗戰精神,具有重要意義。創作者應該直面歷史真實,用戲劇的魅力引領觀眾真切感受抗戰背後的艱難與犧牲、人民英雄的不屈和奮鬥。
(作者為中國國家話劇院院長)
壯哉!沂蒙!
黃定山
2015年,我執導了歌劇《天下黃河》、龍江劇《松江魂》。2018年,我執導了民族歌劇《沂蒙山》。我的很多紅色題材創作,都與抗戰相關。那栩栩如生的抗戰英雄和人民的形象,令我不能忘、永不忘。
“如果他已犧牲,這孩子托你哺養……沂蒙的女兒還叫沂蒙。”劇中《沂蒙女兒》的唱段,讓多少觀眾潸然淚下。至今,民族歌劇《沂蒙山》已演出300多場——我深知,那是千萬觀眾被劇中以海棠、九龍叔、林生、夏荷等為代表的沂蒙人民和八路軍戰士的英雄氣概,被中國人民追求民族解放與自由的必勝信念深深打動的結果。
壯哉!沂蒙!記得排演之初,我們創作團隊沿著八路軍115師東進的路線,走進沂蒙老區。站在孟良崮戰役紀念館的雕塑前,我們久久凝視,思緒萬千;在大青山突圍戰遺址,我們淚流滿面,默默敬獻一束花;在“沂蒙山小調”紀念地,我們聆聽大山裏飄蕩著那熟悉而優美的旋律;在紅嫂故里,我們常被她們無私的情懷震撼……腳踏曾經血染的大地,仰天叩問英魂的期許,一次次深入采風,讓沂蒙精神在我們心中立體起來。
沂蒙紅嫂是革命戰爭年代沂蒙革命根據地出現的一個偉大群體。她們送子送夫參軍支前,捨生忘死救護傷員,撫養革命後代。用乳汁救小戰士的明德英、創辦戰時託兒所的王換于、帶領婦女用門板架橋的李桂芳等,都是沂蒙紅嫂的典型代表。民族歌劇《沂蒙山》中的海棠這一藝術形象,正是千萬個沂蒙紅嫂群體形象的縮影。她的形象詮釋著“英雄性與人民性的統一”,她的力量來自樸素的善良和堅定的信念,這使她的形象更加真實、可信、動人。
我常説,紅色題材的創作,最關鍵是創作者是否發自內心相信。我説我相信!我每次創作都滿懷深情,心生敬意。我相信烽火歲月的悲壯與真實,相信英雄對真善美的追求,相信他們的奉獻情懷,相信一個人因信仰能爆發出我們稱之為“壯舉”的巨大能量!血染青山春又生。淚水依然滾燙,留給歲月的芳華銘刻榮光。
(作者為一級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