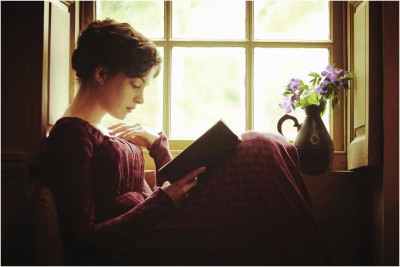
圖為電影《成為簡·奧斯汀》中,演員安妮·海瑟薇飾演的簡·奧斯汀正沉浸書中世界,令人不忍叨擾。
不少電影裏都會出現主角捧讀的鏡頭,一本出鏡不過兩三秒的書有可能與整部影片遙相呼應,等待著細心的讀者去勘破,一旦破解,便忍不住拍案叫絕。
剛剛閉幕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愛樂之城》斬獲6項大獎,當人們津津樂道這部熱門歌舞片中“向經典歌舞片致敬的89個梗”時,有讀者發現了《愛樂之城》中唯一致敬的一部圖書——《英雄之旅》。
在男女主角第4次相遇的聚會上,一名鬍子拉碴的製片人問米婭:你聽説過約瑟夫·坎貝爾嗎?米婭點頭説:是的。製片人帶著幾分得意的神情繼續説:我打算重拍金髮女孩與三隻熊;另外,《英雄之旅》,我會擁有它的經營權。可以説,《愛樂之城》的這個情景揭開了好萊塢編劇對坎貝爾無限崇拜的冰山一角。細細品味電影女主角的追夢之旅,倒與坎貝爾提出的“英雄之旅”模式有幾分吻合。
電影主人公談論、捧讀的一本本書一首首詩歌作品,其中包含了導演編劇怎樣的匠心?回首近些年大銀幕,主打硬科幻的《星際穿越》意外發酵了狄蘭·托馬斯知名詩句“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文藝片《賽末點》男主角翻閱的《罪與罰》暗示了他本人的命運走向。這些經典圖書或詩篇在影片中不僅僅是附贈“彩蛋”或裝飾品,而是在結構或主題上與影片彼此打量、互為照亮。
在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湯惟傑看來,無論是串聯劇情,抑或展現角色波瀾微妙的心理,當大眾流行文化與純文學恰到好處地交織在同一層面時,經典篇目與銀幕敘事成功共享、共情、共鳴,一種奇妙的共振感便會向觀眾湧來——文學擁有了聲光色影的血肉支撐,影片被注入了人文哲思,觀眾和讀者由此獲得更為豐富的美學享受。與其説哪一種藝術樣式成就了另外一種,毋寧講這是影視與文學相擁後雙重觸動了人們的心弦。
影視故事的伏筆,原來隱藏在一本本書裏
有人評論,作為“寫給洛杉磯的情書”,《愛樂之城》深諳好萊塢影視業心照不宣的秘訣之一,那就是被諸多編劇青睞的坎貝爾——他總結的“啟程-啟蒙-考驗-歸來”英雄敘述模式,影響了眾多創作者,也成為不少超級英雄電影的模式“寶典”。比如《星球大戰》導演喬治·盧卡斯曾偶然翻閱坎貝爾的書,一下子就迷上對神話歷程的分析。《千面英雄》成為《星球大戰》的重要靈感來源,坎貝爾也化身盧卡斯追隨的精神導師。此外,《獅子王》《駭客帝國》《哈利·波特》《奪寶奇兵》等電影創作都受到這一模式的啟發。
簡單地説,英雄出發上路,進入神秘迷人的異常世界,經受考驗,經歷了儀式化的數個階段後,主人公升級自我,獲得成長。不少好萊塢大片都遵循“英雄之旅”模式展開敘述,這也引發了業內對“超級英雄”易陷入扁平化窠臼的指摘。
不難發現,文學讀物在電影中往往牽出一條條線索。影評人丁曉潔曾作過一番有趣總結:三流導演讓主角隨手拿上一本書作道具,二流導演以閱讀口味彰顯主角的身份和性格,對一流導演來説這卻是價值觀層面的事,他們每選擇一本書都埋下一個彩蛋———你讀什麼,決定著你走向何方。
拿哪本書,在電影中大有講究。知名導演伍迪·艾倫對“植入”文學彩蛋頗有心得,他的影片《賽末點》就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了一把。男主角威爾頓躺在床上閱讀企鵝書屋出版的《罪與罰》,對這名從愛爾蘭到倫敦當網球教練、企圖融入上流社會的窮小子來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有用的談資,他也正是通過談論陀式作品獲取了岳父好感。巧合的是,《罪與罰》的情節活脫脫就是男主角命運的翻版,書中青年大學生走投無路,鋌而走險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為了滅口又害死妹妹,因種種巧合逃脫法律處罰,卻被另一種來自心靈和道德的懲戒所困束———這不正是《賽末點》男主角的人生預言嗎?有學者評價,伍迪·艾倫安排男主角讀《罪與罰》,除了向摯愛的作家致敬之外,恐怕也同樣向觀眾昭示著影片走向和主題。
詩句點睛,與電影敘事調和出迷人的張力
在評論家木葉看來,除了埋下伏筆與暗示,有力度的文學作品,往往能提升電影的敘事高度,仿若一盞人文聚光燈,照亮並抵達了“靈魂的深”,為影視畫面注入詩意。
不少影評人對休·格蘭特主演的《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中那首《葬禮藍調》唸唸不忘。英國著名詩人奧登的詩句悲愴凝練:“不再需要星星,把每一顆都摘掉/把月亮包起,拆除太陽/傾瀉大海,掃除森林……”當這首詩被緩緩吐出,成就了全片最嚴肅沉痛的華彩,與此前的輕鬆、幽默、浪漫片段構成一股奇異的張力,全片達到精緻的平衡。
同樣,周星馳在“無厘頭”電影《喜劇之王》裏飾演跑龍套的演員時,不忘埋頭研讀斯坦尼斯拉伕斯基《演員的自我修養》,一部頗具學院派意味的理論著作,在周氏搞笑風格裏,自帶幾分荒謬多少辛酸,意想不到的反差張力呼之欲出。
誰説這不是電影借文學之口的深情訴説呢?《星際穿越》中,宇航員父親因時空穿越進入多重時空,當載著人類生存希望的飛船駛向太空,老布蘭德博士吟出詩句:“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老年應當在日暮時燃燒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迸發出不屈的生命能量。這首狄蘭·托馬斯的知名詩歌《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將人本身的衰老病死,演化為時間對人的追獵,與影片隱含的主題珠聯璧合。
狄蘭當初寫這首詩來鼓勵病重的父親,而導演諾蘭賦予了詩句深層次的解讀,“不要溫和地走進那個良夜”,不僅僅是個體的臨終怒吼,還寓意整個人類、星球的命運豈能堙沒于黑洞。在評論界看來,詩歌與影片的貼切,仿佛詩人在近一個世紀前就得到了劇透。而諾蘭和狄蘭相似之處在於,他們思索“生、死、愛”的哲學主題,懷著勇氣和意志去化解白晝與黑暗、生與死的對峙;同樣,藝術和科學也好奇共通的命題:關於時間、空間,關於人類掙脫時空之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