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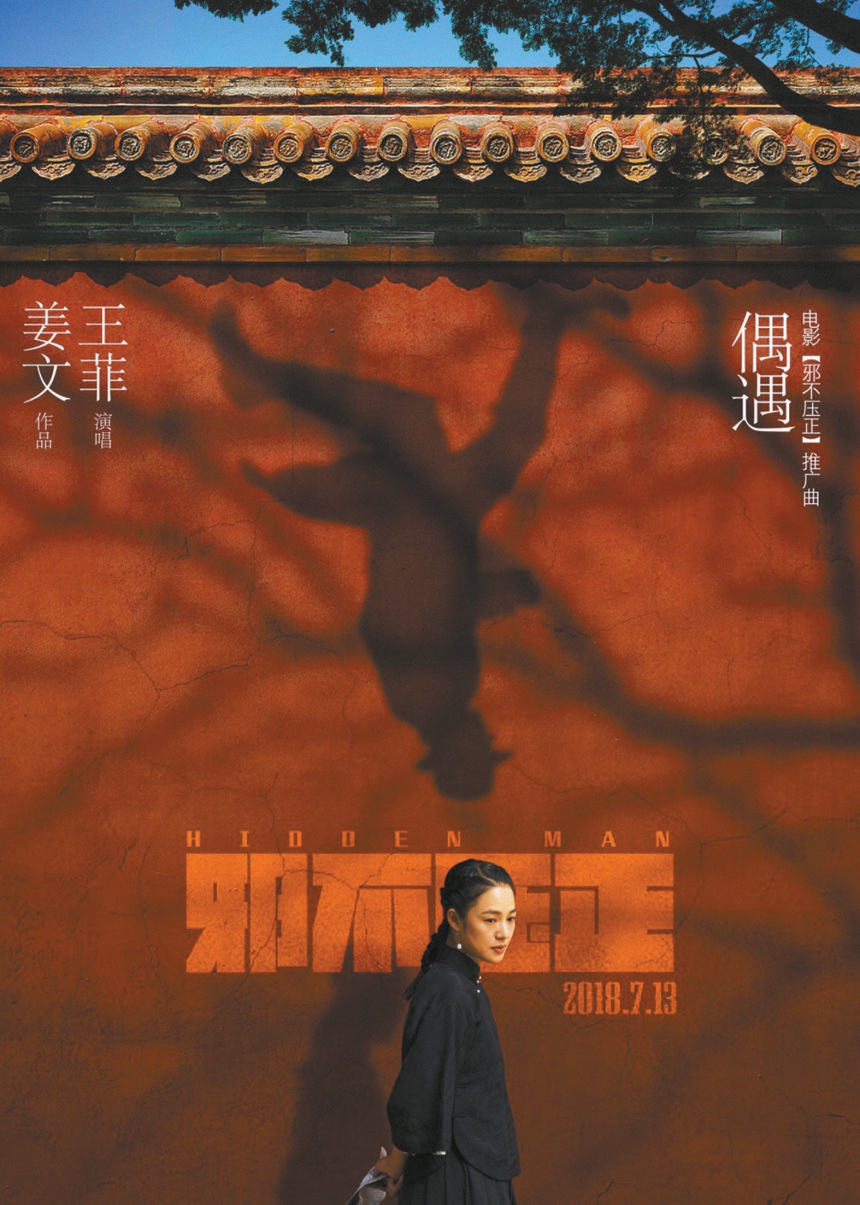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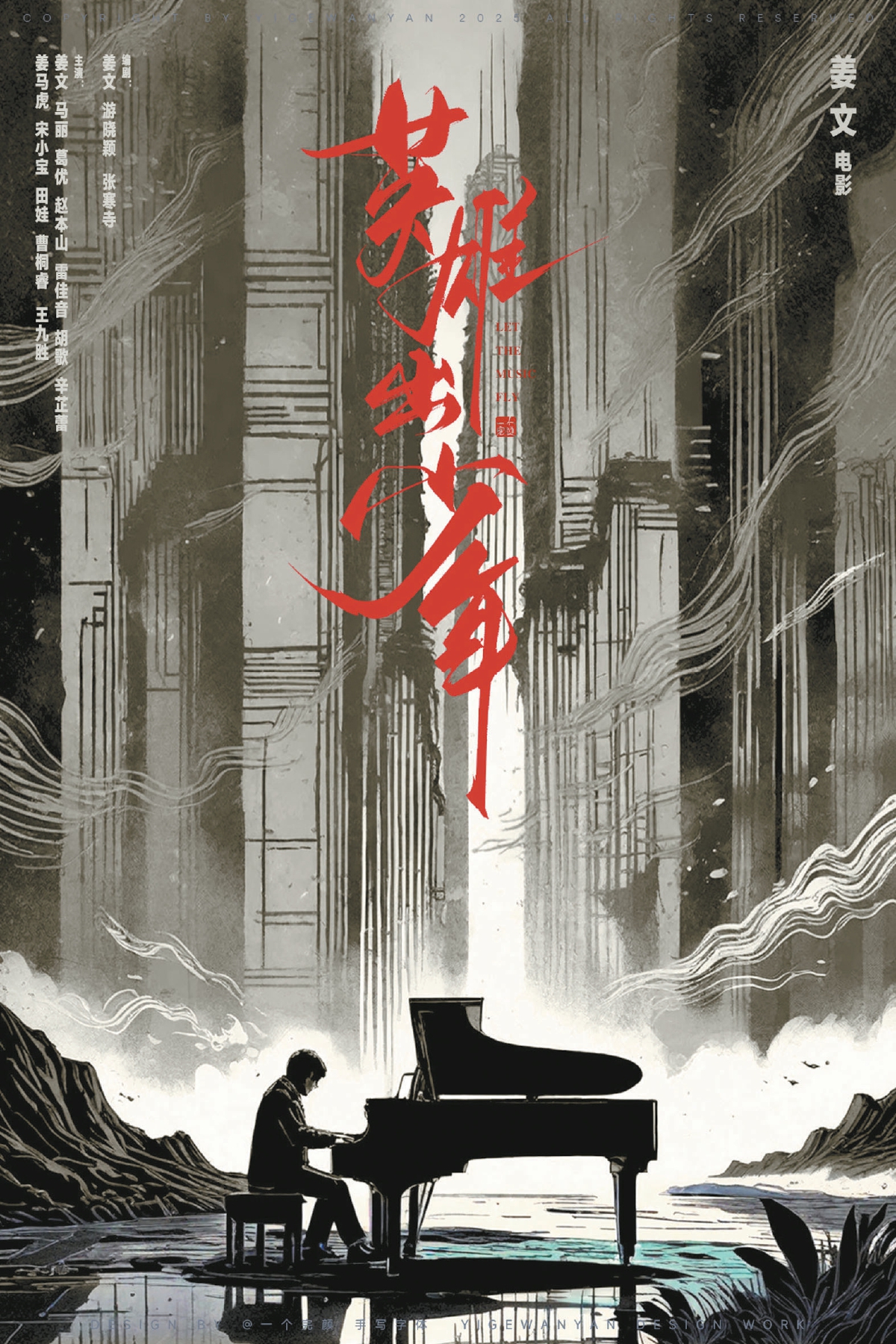

4月25日,第十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迎來備受期待的姜文電影大師班。姜文甫一亮相,觀眾席的手機屏立刻化作星海閃爍,大家的目光透過鏡頭聚焦舞台中央,姜文以一貫的灑脫調侃開場,他提議大家把手機放下,“咱們聊聊天,你老舉著手機,腦子就放空了。別用手機記,要用腦子記事。手機記的不等於你記的,它當你的腦子外挂可以,但是你不能把你的腦子完全拜託給它,我今年62歲了,依然能夠用腦子記,都能記得住。”
姜文笑説自己60歲以後的一個特點就是話多,“別説讓我説一個半小時,我講15個小時也行,我現在話特別多。我摟著點兒,別你們待會兒煩了,説我‘爹味兒’。但我也不能假裝我不是爹,我就是爹,我這年紀快當爺爺了,不能假裝還是一少年,裝萌,有點不好意思。”
日前在北影節評委見面會上,姜文曾説:“不要隨便評論一部電影,也不要隨便寫影評”,此話一齣即被熱議,在大師班現場,他解釋道:“我不是不讓寫影評,而是不讓‘隨便’寫影評。寫影評是好的,寫得越多越好,但是不能隨便。隨便兩個字很害人。我拍電影的時候堅決不隨便,隨便首先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生命。”
整場大師班,“老薑”真誠幽默,金句頻出,場內不時傳出掌聲與笑聲。而在歡笑之中,姜文毫無保留地為大家分享了創作前、中、後期多個維度的經驗,也給予了行業後輩很多鼓勵,可謂幹貨滿滿。
每個人看電影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樣子
擔任本屆北影節評委會主席的姜文是中國電影中的一個獨特存在——他以過人的才華,在編、導、演的多重維度上不斷突破創作的邊界。他曾出演《有話好好説》《宋家皇朝》《本命年》等多部膾炙人口的作品,並以《太陽照常升起》《一步之遙》等導演作品,入圍國際頂尖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並獲得重要獎項。他的藝術風格兼具野性浪漫與深度思索,無論是作為演員的爆發力,還是作為編劇、導演的創作力,都透露出強烈的個人印記——粗糲中見浪漫,戲謔裏藏鋒芒,在商業大潮席捲電影産業的今天,他始終秉持著清醒的洞察,堅持著創作的本真初心,守護著電影作為藝術表達的先鋒性。
姜文導演作品中,有多部是根據知名小説改編,有趣的是,姜文的電影對原著小説改編很大,他的電影完全成為另外一個模樣。既然改動這麼大,何必花錢買版權,付改編費?姜文笑説自己的父親也曾問過他這個問題,“省點錢不好嗎?”姜文當時“糊弄”父親的理由是:“我要有個幫手,有個小説衝在前面,不至於別人第一棍子打到我這兒,但實際上人家不會打小説,人家就打你。”
玩笑過後,姜文表示,其實每個人看電影、看小説,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樣子,“就像魯迅説看《紅樓夢》,‘你是誰,你就會看到什麼’。”姜文拍的電影就是自己看小説時的樣子,他最初也沒有意識到改動很大,“不是故意的,等發現改動太大時,沒有辦法,回不來了。”另一方面,姜文坦承,如果沒有小説的刺激,也不會有他腦中的故事,不會有電影,“所以沒小説不行,完全是它也不行。”
姜文説曾有一位主持人問他,小説《俠隱》裏吃喝玩樂的情節,為什麼在他的電影《邪不壓正》裏都沒了?姜文説:“我對吃喝玩樂不是很有興趣,所以,我電影裏面儘量不拍吃飯的戲,吃飯在我的電影裏不那麼重要。另外,我在《俠隱》中看到的是我認為的老北京,那是我感興趣的。”
姜文導演的作品總是會被影迷進行解讀,分析他哪句臺詞、情節有哪些隱喻,姜文説自己創作時完全想不到這些,“沒有任何隱喻。我在中戲學習了四年表演,對此做了很多研究,演一個人,要通過資料、想像等精確對人物的理解,越精確你對這個人物就越來越熟悉,越熟悉就會越精確,在表演時這是從簡單到複雜,又從複雜回到簡單的過程。和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是一個道理。就像武術,練的時候不能想著打什麼東西,得把練變成潛意識。所以,創作就是表達你的潛意識,那個時候你再想著隱喻這些,那就完了,但是不創作、讀書的時候,你該怎麼想就怎麼想,那是訓練階段。”
沒有態度就沒有幽默,沒有幽默就沒有戲劇
很少有將姜文定義為喜劇導演,但他的電影卻被評價為“高級的幽默”,談及何以會形成這種電影風格,姜文回憶説他上中戲時,老師張仁裏反復和他們強調:沒有幽默,就什麼都沒有。姜文説:“如果不幽默,你上來就是演一件事兒,事兒不是戲。做一個報告,説一段通知,這沒意思。幽默其實就是你如何看待一件事兒,你對事兒的態度,沒有態度就沒有幽默,沒有幽默就沒有戲劇,沒有戲劇哪來的電影?按照西方的説法,如果沒有幽默,甚至人格都有缺陷。”
隨後,姜文補充説,觀眾看到某段戲笑了,這段戲不一定就是喜劇,“人其實生活在很尷尬的狀態裏,你反正得死,但是你還要玩兒命活。你活得再好也得死,這就是人生,人生本身就有點荒誕。人的生命形態本身就很有意思,我們根本不用去製造喜劇。”
電影中那些經典的幽默橋段和臺詞是否有即興創作臨時加的?姜文表示,電影包含了創作者的態度。“我所有電影沒有任何臨時加的臺詞,寫劇本的階段非常重要,就是在錘鍊這部電影。當然也可以臨時加詞,但是效果並不好。我是演話劇出身,我知道臨場發揮是多麼重要,同時是多麼難。很多人現在願意演喜劇,甚至去鍛鍊幽默感,但我覺得這是練不出來的,沒法兒練。現在大家都説‘梗’,這是從相聲中的哏兒帶出來的吧?不是人人都是馬三立、侯寶林,就算把他們的臺詞給你,你講出來也沒意思。在相聲大師們面前,我們只能當觀眾。卓別林的電影,你重拍一遍也沒有卓別林的好看,所以,我們得相信有些人是唯一的,有些事兒是唯一的,不是靠設計出來的。”
現場從來不看劇本,因為寫完劇本電影就已經有了
對於劇本,姜文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的,他認為創作的必要性前提是要理解人物本身,創作者必須了解人物的時代背景、人物的所遇所求。他以AI大模型為喻,分享劇本寫作模式:“寫劇本就好像現在的AI大模型,比如説現在這個場子,你在腦子裏有一個模型出來,其中第六排的一個人,你在寫他,如果你對整個事情沒有概念,甚至沒有其他不出場人物設計的模型在腦子裏,你就不知道怎麼寫。我寫劇本的時候不累,但是弄這個模型的時候比較累。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裏,環境周圍應該是什麼,甚至天氣環境、人文環境、歷史環境等等,這些你清楚了,你再拎出這幾個人物寫,就不累,很有快感。”
姜文認為寫劇本要理解人物,“這不是一個通過技術可以解決的問題,你真的得有時間去認識這件事,否則寫出來的東西不值得看。人物會説什麼話,為什麼是這樣的人物關係,前期準備劇本産生的過程,是學電影的人要特別注意的。”
姜文説他的電影都是自己寫劇本,寫時就想好了要拍什麼。“比如《讓子彈飛》,湯師爺死了,張麻子最後回來了,很多人説他沒必要回來,劫道搶完錢就走,片子時長還能短點。但是對我來説,這不是我要拍的電影,為了最後張麻子回來這個事兒,我們在劇本創作期寫了很多版本,最後是一個笑話給了靈感,僅僅是為了這個情節設計,我們就想了半年。”
相比于一些製作圖文精美的劇本,姜文表示,他的劇本是為了拍電影用的,“不是為了創投也不是為了發表,我是把大家討論的精華變成劇本,這個劇本最重要的作用是幫助我實現這個故事。現場我從來不看劇本,因為我寫完劇本,電影就已經有了,臺詞也記住了。我在腦子裏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在拍攝現場就是把我腦子裏看到的電影拍下來。這個劇本拿到創投或出版社可能真的不好,它不標準。”
當導演千萬別罵演員,不要成為扮演導演的導演
姜文對於導演的建議是——“不要成為扮演導演的導演”。他認為導演在現場的主要任務是服務好大家,為各部門創造良好的工作氛圍,圓滿地完成拍攝。“我找了葛優、周潤發,我要把葛優變成周潤發,把周潤發變成葛優,那我何必呢?葛優就當葛優來拍,周潤發就當周潤發來拍,千萬別逼著葛優變成周潤發,這太難為人家了。讓葛優和周潤發都發揮他們各自的高度,這是可以的。還有些導演,非要演員受點傷,非要真打,這樣不好。不能逼著演員做痛苦的事,假的拍得逼真,那是導演的真本事,而不是讓演員骨斷筋折。大家都要很快樂地拍電影,千萬別讓人家受苦受累受罪。”
問姜文如何給演員帶來情緒價值,他笑説自己做法很簡單,“就是‘吹捧’,讓演員高興得忘乎所以。他只有忘乎所以的時候才能做出各種你想要的東西,不要老批評他,會演不好。導演行使權力的做派特別不好,要愛護演員。”
可能與自己也是演員有關,姜文表示演員在片場很不容易,“他要暴露他的情感,好演員不是裝的。比如現在演他母親去世了,他得真去找令他痛苦的東西,可能真的會想到家人去世的痛苦樣子,他平常都不願意面對,為了這個戲,他必須把它暴露出來。還比如拍人性惡的一面,演員也要被逼著暴露出來。這時候演員挺需要保護的,要愛護演員。”姜文電影中還經常啟用非職業演員,在他看來演員沒有職業和非職業之分,“只要他穿上那身衣服,在那個情境裏,都是演員。”
提到後期製作的剪輯的話題,姜文認同剪輯的重要性,電影是剪輯出來的藝術,有時同樣的素材在不同的剪輯師手中,呈現的效果也會天差地別。但他説自己的作品不會在剪輯時做出重大內容調整,因為所有需要呈現的內容在劇本創作階段都已經定型。
為闡釋這種創作理念的差異,姜文以親身參演的《星球大戰外傳:俠盜一號》和影史經典《亂世佳人》為例——這兩部作品恰恰體現了好萊塢工業體系中常見的“後期補拍修正”創作模式。姜文指出這種集體創作機制下,確實存在通過後期大規模補拍、修改來重塑故事的可能,但強調創作方法必須與作品屬性相匹配,像《教父》這樣具有強烈作者屬性的作品,是無法通過後期手段來實現藝術表達的。
這些電影缺什麼非得你來不可,這很重要
在姜文看來,年輕人想拍電影,最重要的是他要有一個人生態度。“真想拍電影,先問問自己,你有什麼要表達的。如果你沒什麼要表達的,那也拍不好。電影技術那部分是工具、是話筒,但你要説什麼很重要。如果沒有自己的態度、自己要説的話,那你會很受罪,幹起活來也會很難受。你先問問自己你要表達什麼,到今天為止,這些電影缺什麼非得你來不可,我覺得這很重要。”
姜文説他和北京電影學院的學生交流,有些學生説畢業後不知道要做什麼,“我覺得他們應該想幹什麼才好,多做你們想做的事兒。當然壓力是有,可是少點抱怨多行動是最好的,因為你們真的能幹出很多成就來,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姜文舉例説,他的新片《英雄出少年》講述了一個天才少年成為鋼琴家的故事。“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天才,他父親告訴他是,結果他就是了。這種有才華的人其實很多,只是可惜錯過了。我自己不識譜,這次為了拍電影,嘗試著學鋼琴,居然發現很快就能左右手彈貝多芬的曲子。所以我想和年輕人説,只要你們試一試,肯定會有驚喜,你比你自己想像得要優秀。你可能就是被手機耽誤了,你少玩點手機真的能夠做好多事兒。”
電影拼的不是技術,是表達的內容
面對如今飛速的科技進步、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用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接觸電影技術,但姜文始終認為,尖端的設備和産品並不意味著可以産出更加精良的作品,一部電影作品,最重要的還是要回歸到內容層面:“凡是技術可以解決的問題,現在操作起來是比以前更容易了。但最頂層的那部分內容最後還得靠人,沒有人,做不到。電影拼的不是技術,拼的是表達的內容。”
姜文説自己不是“技術控”,他著迷的是表達的內容。“現在所有人都可以寫一篇短文甚至小説發在網上,是不是當作家更容易了?我覺得更難,你想寫得出類拔萃比原來還難。現在剪輯和電影設備確實比原來好了,我有時候在飛機上隨便看一個電影,發現這電影技術各方面拍得真好,是上世紀90年代電影難以企及的程度,但是這電影仍然不是好電影,為什麼?劇本太差了,拿這麼好的技術聊這麼簡單的事兒,或者説聊這麼無聊的事兒。”姜文説他拍電影追求的目標是觀眾看著不能累,“你自己的拍攝過程都可以受累,但是電影放的時候,觀眾看得要賞心悅目。”
對於觀眾對自己作品的解讀,姜文則持包容的態度:“假如解讀可以一石激起千層浪,那是好事。激起的浪越多越有意思。”他更是以“蒙娜麗莎”為例,生動闡釋“好看”和“看懂”之間的關係:“蒙娜麗莎在那兒微笑那麼多年了,你能懂她笑什麼呢?你説不行我必須得明白,你把蒙娜麗莎的嘴撬開,利用AI技術讓蒙娜麗莎説説蒙姐你樂啥呢?你看看蒙姐説出來的答案,是比她不説強呢,還是説出來更好。蒙姐不吭聲的時候,我覺得挺好,有點神秘感。當然蒙姐開口説話,也不是不行,看個人喜好。”
雖然姜文説不喜歡拍吃飯的戲,但是《邪不壓正》裏面有一句很經典的臺詞,“為了這點醋,我們得包一頓餃子。”一説這句臺詞,姜文立刻想到了《哪吒》系列的導演餃子,姜文稱讚説:“他做了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兒。但是我認為這是開始,這不是最高點。這裡藏了那麼多餃子呢,餃子哪有上一個的,怎麼也得上一盤吧?得一盤一盤往上端餃子。如果你想拍電影的話,一定要多去嘗試,我特別喜歡那些半路出家的年輕人,中國電影的未來一定會出現更多的‘餃子導演’。”
姜文認為電影需要新鮮血液注入,即使是資深電影人也應常懷新意,“大家看電影就想看點新鮮,老一樣就沒意思了。我覺得電影最可怕的是都特別像,假裝特內行,特別專業,其實都特別像,像不好。”
整場電影大師班持續近兩個小時,姜文以一貫的真誠、坦率、幽默和犀利風格,為觀眾帶來了一場魅力十足的經驗分享。他不只是講述創作,更在不經意間傳遞了一種精神:拍電影不是模倣公式,而是敢於出發、認真思考、絕不隨便。中國電影的今天只是一個開始,年輕創作者要走出屬於自己的路,他們的故事剛剛開始。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供圖/北影節組委會